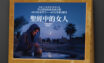《約翰福音六章4節真相探究》
#蝗蟲野蜜讀經圖書館
如因下文圖片未能顯示,也可選擇本書PDF在線觀看:《約翰福音六章4節真相探究》繁版
目錄
編者序
邁克•儒德和尼希米的本系列訪談節目聚焦于《約翰福音》六章4節(“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是否原本存在於新約聖經,逐步展開深入縝密的探究,包括早期教父的著作引文查證、上千份原文手稿的考證、福音書編年時序的合理性研究,最終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也許你會說:“作為一名普通信徒,我有必要在區區一節經文上錙銖必較嗎?這難道不是那些神學家或聖經學者應該研究的事嗎?我為什麼要來閱讀這本書呢?”
我們觀察到,對於聖經的學習,通常有兩類:一是實用主義地學習聖經,只要能解決我的實際問題,有助於屬靈生命成長就夠了,無須關注字句的精准、細節的準確無誤,所以自然會有上面的疑問。另一類是學究型地學習聖經,注重聖經學問的累積,深入各類神學教義的探究,也津津樂道各種爭議的聖經話題——此類也許會對本書的議題產生興趣。
但本書(本系列節目)並非為了迎合大眾的需要,乃是出於對神話語的敬畏,辨明人為的刪減、改變,還原神全備真理的原貌,而不惜花費巨大代價所做的努力。
約6:4是否存在於新約聖經的爭議,會產生非常重要的信仰問題:
- 主耶穌在地上的服事時間是一年多還是(目前大眾所知的說法)三年半?若後者成立,則根據四福音書所記載的事項,就明顯多出一年多的空白期。
- 若約6:4存在,是否表明主耶穌不過逾越節(因為祂並未及時上耶路撒冷過節),並以實際行動廢除了舊約所規定包含節期的律法?從而間接證實,新約時代的信徒也不用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稱妥拉、摩西五經)?
- 若2成立,主耶穌便違反了耶和華的律法,不能成為無瑕疵的羔羊,也違背了祂自己所宣告的“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太5:18)的教訓。
這些問題,關乎我們對基督的認識是否正確,關乎我們今天要怎樣按照聖經的真理去生活,也關乎末後教會多大程度上行在神至高至聖的旨意當中,成為榮耀的教會!
我們已經進入末世,很多人引用先知以賽亞的預言來描述當下時刻:“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賽60:1-2)我們已經切實感受到黑夜的逼近,耶和華的榮耀如何發現照耀在祂子民的身上,如同使徒時期的教會一般?甚至比那時更加榮耀?因為“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哈該書2:9)。
恢復祂話語的全貌!一點一劃都要恢復!一切被仇敵偷竊、搶奪、扭曲、毀壞的字句都要恢復!因為祂話語的權能超過核氫彈,將震動天地!當祂的子民如同基督一般,完全活出祂全備真實的話語時,榮耀將伴隨著這些神的眾子們,全宇宙將迎來榮耀的千禧年國度!(“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挾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8:19-20)
“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徒3:21),萬物復興,神的話語首先要恢復!邁克•儒德和尼希米團隊所做的工作,正是實現末後復興偉大藍圖中的重要一環!恢復神的話語,預備道路,迎接彌賽亞!
第一章 引入歧途,還是事出有因?
一、編者概述
邁克·儒德在他的《編年體福音書》中將《約翰福音》六章4節刪去的做法,引起一些人甚至是某些彌賽亞信徒的責備。那麼,邁克究竟是將人引入歧途,還是有充分的聖經手稿依據?在《安息日晚間直播》節目的三人小組論壇,“《約翰福音》六章4節屬於聖經嗎”,成為尼希米、約翰·拉爾凱和邁克·儒德共同探討的主題。
這也是尼希米團隊數月以來研究成果的彙編和彙報。該團隊包括:對此主題深入查考數百個小時的約翰·拉爾凱,大家並不陌生的丁字牛排先生,希臘本土的一名博士,和其他希臘古文學者們……。他們並非簡單的贊成或否定邁克的觀點,而是實事求是從原文手稿來查考證據。本系列節目共有四集,按照縝密的邏輯關係和學術思辨,為大家層層展開這部分的聖經真理。
通過《使徒行傳》二十一章25節經文舉例,論壇小組給我們提供了重要思維範式,不再是翻譯技術上的差異或疏忽,而是:我們應該相信哪一份手稿?尼希米鼓勵大家不要輕信任何人的觀點,包括邁克·儒德。他們將羅列足夠多的原文證據,把最終選擇權交給觀眾朋友和看到這資訊的每一個人。
在三人小組正式進入主題之前,邁克·儒德解釋了《約翰福音》六章4節的背景,可謂一氣呵成,對這之前、四福音書中耶穌做的每一件事的講述極為精彩,再次讓我們領略《編年體福音書》的魅力,為接下來的探討正式拉開了帷幕。
二、約6: 4爭議起因
【邁克】(以下簡稱“邁”)去年我不能去耶路撒冷,尼希米在那裡待了幾個月,他回來後開始向我講述那段時期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對此我感到非常激動,並當即決定邀請他一起過逾越節,因為這是為每一個人所預備的。
隨後他在12月份拜訪了我們,那天晚上我們私下聊了好幾個小時,根本沒法把所有內容都塞進來。現在我要把話題交給尼希米,讓他給大家講解。在《安息日晚間直播》[1]最近幾期節目當中,他已經涉及了其中一些內容,不過這回是完整地解釋它們的來龍去脈。女士們,先生們,請與我一同歡迎尼希米·戈登!
【尼希米】(以下簡稱“尼”)對於今天我們要分享的內容,我感到非常激動。這是數月以來我一直在做的事。
一切還要從幾個月前說起,當時我和一個人坐在一起,他很嚴厲地責備了我。他說:“你怎麼能和邁克·儒德攪合在一起?邁克·儒德根本是在把人們引入歧途!”,我回答他說:“邁克怎麼把人們引入歧途了呢?願聞其詳。”
這有點諷刺,因為這個人是位彌賽亞信徒。我對他說:“比起我來,您和邁克之間的共同點更多呀。所以,您怎麼會認為邁克把人引入歧途了呢?”他最後說道:“就是《約翰福音》六章4節!邁克告訴人們,聖經裡本來沒有《約翰福音》六章4節。他刪減了聖經的內容,他怎麼敢這麼做!”
我認真聽了這人的陳述,他不是第一個這樣說的人。我聽過相當多人這樣說,他們不斷提到這節經文,對我來說這有點奇怪,因為我不是彌賽亞信徒,也不是基督徒,這不過是一句經文而已。倘若有人對我說:“你瞧,《申命記》六章4節的‘聽啊……’這個字不在妥拉中。”我會覺得根本不用談這個問題;但如果是《創世紀》十章或二十六章,我想或許還可以談一談:給我看看缺失部分的手稿,這樣我們可以探討一下。
老實說,我其實不太了解約6: 4,邁克會解釋為什麼它這麼重要,但我其實很難完全領會它的意義。就在那個人向我解釋的過程中,我對他說:“這樣吧,我去查查看這一節,如果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邁克的觀點,那我自己會去找邁克,並會糾正他說:‘邁克,根本沒有證據支持您的觀點,您可不能這樣教導關於《約翰福音》六章4節的內容。’”
第二天早上,我和身邊這位約翰·拉爾凱一起吃早餐。當時還有第三個人與我們一起,我對大家說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這不是我第一次談及這個問題。與我們一同吃早餐的另一人突然大聲說道:“我能證明邁克對於約6: 4的解釋是錯的。”我說:“太好了!我們終於能有點進展了,快告訴我們,證據是什麼?”他說:“我問過了一位研究手稿方面的專家,他告訴我,邁克弄錯了。”我說:“好吧,可這只是某位專家的觀點,或許他是對的。”那真是一位很有名氣的專家,“但我得自己去查查看,我也可以解讀手稿。”
三、尼希米研究團隊簡介
我邀請約翰來到這裡,我對他說:“能請你幫我查查《約翰福音》六章4節嗎?看看是否有證據支持邁克的觀點?”我無法證明邁克到底是對還是錯,這取決於是否有確切的證據。而我所能做的——也是我的專長——就是去查看是否有證據支持他的觀點立場;或者那只是他隨口說說的不切實際的理論?只因為他不喜歡這段經文,就決定把它從中聖經中抹掉?這兩者之間存在很大差別。
而當時我所不知道的是,這位朋友約翰,已經花了40個小時研究這個問題,並且進行了幾百個小時的深入查考。這是一次國際性的協作:我和約翰參與到其中,還有“丁骨”(T-Bone)先生,他真是神派來的,幫我們查閱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手稿,研究那些我可能要花費一生才能完成的內容。他三天就完成了,讓我們為丁骨先生喝彩吧!
在希臘,有一個人也一直在幫助我們這個項目,他就是Pavos Fasliatis博士。有時,我們會發現一些不太瞭解的東西,或者感覺哪裡不太對勁的。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我就把它交給這位希臘語專家去校對。有時他又把它轉交其他希臘語專家,所以,世界頂尖的希臘古文書學者們都在研究這個問題,他們一直在幫助我們進行這項事工。我們和希臘語新約[2]事工的負責人談過了,我們諮詢了各個領域很多頂尖學者,因為我想知道到底有沒有證據支持邁克的觀點。
我想再強調一遍,我不會告訴你們最終結論,是否要相信和贊同邁克的觀點。我所做的是給你們提供現有證據,由你們自己決定。
所以,當我們一起吃早餐時,那個人說:“我能證明這一點。”我就回答:“好啊,我接受挑戰。”從那以後我便歷經了許多個不眠之夜,致力於這項研究。有時候我一天要做16到18個小時,因為我想要得到答案。
四、徒21: 25節原文查證
我們將要談論的是一件很嚴肅的事,關於約6:4,全球超過十億人都相信這一處是出於神的聖言,而邁克卻說,這一句應該從聖經中刪掉。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很嚴肅地對待這件事。就像我剛才說的,如果這是《創世紀》十章29節或者別的章節,寫在那裡的每一個字母於我而言都是神的話;即便是一些不重要的章節,比如日子等等諸如此類,於我而言仍然很重要。
我巴不得立刻和大家探討《約翰福音》六章4節,但在此之前,要知道這件事茲事體大,我必須先探討《使徒行傳》二十一章25節的經文。
其實一開始是約翰向我提起的。約翰,請和我們說說你是怎麼談到徒21: 25?
【約翰】(以下簡稱“約”)當時我在和朋友聊天。我們對彌賽亞(耶穌)的信徒應該如何生活,各自有一些不同的見解。我相信,當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時,今天的信徒仍然需要遵守妥拉。但我朋友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認為今天彌賽亞(耶穌)的信徒只需要遵行十誡,僅僅是那十條誡命而已。
我們便就此展開討論。他很熱心,也遵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十誡中的一條。隨後我們談到了十誡以外的內容,他說:“請你在聖經中找出一段,在耶穌受死、埋葬、復活後,門徒仍然遵守妥拉[3]的經文來。”
我們就找到了《使徒行傳》二十一章,那裡說到保羅去見雅各,在耶路撒冷他們討論宣教事工的進展。雅各對保羅說,你看,許多信耶穌的人都對律法熱心,但是我聽到一些關於你的傳言,你教導別人離棄律法。我現在來讀一下聖經裡的原話:“他們聽見人說,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對他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禮,也不要遵行條規。”在雅各看來這是謠言,因為他接下來說,我們要對此採取措施。
【尼】不好意思,我打斷一下,這對雅各來說根本是謠言,可對於今天很多基督徒來說,這卻成為了事實。不是嗎?
【約】遺憾的是,許多基督教教義都建立在對保羅的錯誤指控上。
【尼】這真諷刺啊!
【約】雅各說:“眾人必聽見你來了,這可怎麼辦呢?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吧!我們這裡有四個人,都有願在身。你帶他們去,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替他們拿出規費,叫他們得以剃頭。這樣,眾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的;”所以,雅各在這裡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們得證明那些針對你的傳言都是假的。
【尼】這樣看來,保羅實際上是在維護妥拉,他想通過這個在聖殿的獻祭儀式向人們證明這一點。根據福音書,這發生在耶穌受死、復活之後。根據今天人們的說法,妥拉已經被廢除了。當耶穌說“成了”時,就意味著妥拉結束了。這也正是聖金口約翰[4]所主張的觀點。
【約】就目前我們所讀到的,我倆看法一致。但是到了下一節,他讀的是英王欽定版(KJV)聖經,而我則讀了英文標準版(ESV)。我來讀一下英王欽定版關於這一節是怎麼說的:“你帶他們去,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替他們拿出規費,叫他們得以剃頭。這樣,眾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的;並可知道你自己為人循規蹈矩,遵行律法。至於信主的外邦人,我們已經寫信擬定,他們不需要遵行這樣的事。”
【尼】我的天!諸位,我要再讀一遍這段內容。因為這太重要了。你還沒讀英文標準版(ESV),要不請你先來給我們讀一下這段,看看兩者之間的區別吧。
【約】英文標準版(ESV)完全不一樣,關於這段是這樣寫的,“至於信主的外邦人,我們已經寫信擬定,叫他們謹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與姦淫。”
【尼】這裡有個本質上的區別,我們等一會再來看這一段。我想先帶大家看看雅各在《使徒行傳》十五章所說的話,因為他是在引述先前所發生的事情。當時有人上到早期教會並聲稱,“外邦人若不遵行律法,就不能得救。”大概是指那些法利賽人的規條……
【邁】對,是那些成為耶穌信徒的法利賽人。
【尼】沒錯,我們來看《使徒行傳》十五章20節,雅各說:“只要寫信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換句話說,《使徒行傳》二十一章雅各只是在重申他說過的話,“……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畜的和血。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逢安息日在會堂裡誦讀。”
換句話說,《使徒行傳》這裡討論的,也就是最初稱為耶路撒冷會議[5]上所討論的是,我們這裡有一些非猶太人信徒,我們得裁決是否允許他們進入猶太會堂,成為聖徒的肢體。
法利賽人說:“不行,除非他們也受割禮,還要站在全體拉比面前,然後,他們才可以信耶穌;否則就不能讓他們進來。”而雅各的決定則是:“不,先讓他們從這四件事開始,這四件事是最基本的;至於剩下的,他們每個安息日去會堂就能聽到。”
於我而言,這就如使徒保羅所舉的亞伯拉罕的例子,他說:亞伯拉罕與神立約,他來到迦南地時是75歲,他與神同行的幾十年間都沒有受割禮;一直到99歲時神告訴他,現在你該受割禮了。我想這就是保羅所教導的,而且雅各的看法也一致。
你們都知道,割禮對於成年人來說可不是件小事,哪怕今時今日。在以色列,這項手術也只能在醫院進行,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所以,這裡的觀點是,外邦人信徒可以進猶太會堂聽妥拉,當他們被教導時,就會照著所受的教導去遵行。不要因為他們未受割禮就把他們排除在外,不要禁止他們加入我們。
好,現在我們回到《使徒行傳》二十一章25節,來看看英文標準版(ESV)是怎麼說的:“我們已經寫信擬定,叫他們謹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與姦淫。”
但是在英王欽定版(KJV)裡,也就是約翰和他朋友讀的這一段,這裡多了八個字。希臘文中是六個字,英文版中是八個字,“說到信主的外邦人……”,意思就是“至於那些信主的外邦人,我們已經寫信擬定,他們不需要遵行這樣的事。”這樣的事,指的就是保羅力圖證明自己所遵守的妥拉。
根據英王欽定版(KJV),妥拉只是給保羅這樣的猶太人的,不是給外邦信徒的,外邦信徒只需要遵守那四件最基本的事就行了。這麼說來,外邦信徒可以偷竊、也可以謀殺,只是他們不能吃血?按照英王欽定版(KJV)的意思,外邦信徒豈不是可以做除了這四件事以的任何事?所以,約翰,你正好和朋友談到了這點,你們倆手裡各自是不同的版本,那你會怎麼做?你要如何說服你那位朋友呢?你說服他了嗎?
【約】我不能說我說服了他。首先,我搜集了一些文本注釋,它們幾乎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即這一段只出現在某些手稿中,其它手稿裡則沒有發現相應的內容。所以,一般的結論認為,這一段內容本不屬於聖經。
我們所面臨的根本問題,而且這不僅是我和我朋友之間的問題,任何一個人和三四個人坐在一起,你們都會讀到不同的聖經版本,它們所表達的並不總是完全相同。在這個特殊的例子中,我問我的朋友,我們必須敢於超越我們所看到的英文版的內容。我們有必要仔細研究,以確定聖經最初書寫時所用的字句。我們可以研究這些文本注釋以及手稿的照片,手上也有很多可以查考的資料,從而得出一個很清楚的結論:就是這一段本來不在聖經裡。
【尼】我們能看看有哪些版本存在這個問題嗎?諸位,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很多時候,當你們看到不同的聖經譯本時,他們通常會把相同的內容翻譯成不同的東西。但在這裡他們所翻譯的內容並非不同,而是多出來了幾個字,這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裡有一個列表,約翰把“他們無需遵守這事”這八個字出現的版本放在一起。這是重要的關鍵字,因為“那件事”指的正是妥拉。這是雅各親自教導的。在英王欽定版(KJV)中,他說:“別遵行妥拉”。約翰,請告我們,你找到的不同的版本都有哪些呢?
【約】在NET, ESV, RSV這幾版聖經裡都沒有這句話。大多數現代版本聖經裡都沒有這句話,除了根據《公認文本》[6]翻譯的聖經裡有這句話,比如1611年的英王欽定(KJV)版本聖經,以及一些來源相似的聖經譯本。
【尼】請給大家講講什麼是《公認文本》吧,這名字聽上去很有權威性。對吧,這可是一段被認可的內容,應該來自保羅或者別的某位使徒吧?
【約】那倒未必。我們沒有使徒親筆書寫的原始手稿,也就是他們書寫的福音書,我們只有這些福音書的手抄本。目前已經發現的新約手抄本大約有5800份,每天仍在不斷發掘當中。但是,這些副本的內容並不總是保持一致。所以,必須有人來檢查這些副本的差異之處,並做出決定,我們將使用這個版本或者那個版本的文本。而《使徒行傳》中這個例子正好是存在差異的一個,一個版本這樣寫,而另外幾個版本則那樣寫。
【尼】你提到的這段經文的內容令我很感興趣。據你瞭解,這是不是新約聖經中唯一一處直接告訴信徒不要遵行妥拉呢?
【約】不僅僅是這裡,但這裡的用詞是直截了當的。我們的天父不會讓我們去猜祂的誡命是什麼。我們不需要通過解讀一個寓言來明白:哦,你們不應該犯姦淫。如果祂不想我們犯姦淫,祂就會直說:“你們不可姦淫”。
我們不必把一些解讀弄得複雜化,彼得說過,保羅的書信有些是難懂的。我們不應該通過研究比喻和保羅(編注:而應該從神直接的命令),來決定我們應該如何生活。行為準則以及誡命都是用簡單明瞭的語言表達的。在英王欽定版(KJV)聖經裡,我們卻看到了相反的明確指示:不必遵行妥拉,外邦信徒不必遵守這樣的事。
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為這帶來嚴重分歧。文體差異的確存在,而大多數文體差異與你持守信仰以及日常生活並無關聯。但在這個例子當中,有一個版本告訴我們不必遵行妥拉。如果沒有這多出來的一句,發生在《使徒行傳》二十一章的故事就是最有力的例證,說明那些相信新約的信徒們,在彌賽亞耶穌受死、埋葬和復活以後仍然對妥拉熱心,且遵行妥拉。
【尼】諸位,我想先跳到塔納赫[7]的某處,因為我是從舊約聖經為出發點的。當我讀塔納赫時 我們也會遇到所謂的文體差異。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並沒有最初的妥拉的複製版,即約書亞寫在蓋滿灰泥的石版上的——這記載於《約書亞記》;我們也沒有最初摩西所寫的妥拉。我們必須得複製再複製,然後查閱不同的手稿並且將它們相互對比,然後我們才會試著瞭解最初的話語是什麼。
有時候差別是很細微的。比如,《出埃及記》十五章那裡有個很具代表性的例子。那裡說:“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聖所”,在一些手稿中,使用了“耶和華”而不是“主”這個稱謂,這的確挺重要的。不過,其實“主(Adonai)”和“耶和華(Yehovah)”,都是指同一位神,二者所表達的資訊並沒有不同。
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英王欽定版(KJV)和其它聖經譯本的差異,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本的資訊內容。“無需遵守這事”是一個相當顯著的差異。我之所以特別喜歡這個例子,是因為除了那些唯讀英王欽定版(KJV)的人以外,沒有人質疑這六個希臘文單詞——當然英文是八個字——它們是否是被添加的。但有趣的是,它們的確是在相對較早的時期被添加的。
我們有一份重要的文獻《伯撒抄本》[8]。它寫於西元五世紀,並且這裡包含了這六個字。我很欣賞約翰在這裡所做的,他翻閱了許多手稿,看看它們當中哪些包含這六個字,哪些則不包含。他基本上自學了希臘文,所以,他能讀懂並辨認出手稿中這些文字。《伯撒抄本》中包含了這六個字,它在西元五世紀時說“無需遵守這事”,可以說是很早期了。
《聖耶福列木再撰抄本》[9]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手抄本,它就是所謂的“翻版複寫”[10]。“翻版複寫”意思就是指它可以被循環再利用。他們拿走原本的福音書,刮掉上面的文字,然後在上面寫上不同的內容。十九世紀的學者們所做的,就是用顯微鏡來觀察這些書卷,並且拍攝特殊類型的照片。這樣他們就能讀出被抹掉的文字。我們在這個五世紀的翻版複寫原稿中所標記的,可以看到有六個希臘字“無需遵守這事”。
現在我們有兩個見證人了。我們可以說,任何事都要憑兩三個人作見證。但是,當你有兩個見證人,他們所說的正好與你的主張相反,你會怎麼做呢?
這是西元四世紀的西奈抄本[11],我們用紅色標注的地方,可以看出那六個希臘字是不存在的。如果文本中有這六個字的話,它們就應該在這個位置,但在四世紀的西奈抄本中並未發現它們的身影。四世紀的《梵蒂岡抄本》[12],也沒有這些字。我們用紅色標注的部分就是被增加的文字所在的地方。
現在,我們有兩個不同的版本。約翰,我特別喜歡你告訴我的這個故事是在於,到最後你和你的朋友在電話裡,他說,你有你的聖經,而我有我的聖經,它們不一樣,在一個版本裡,有這麼幾個字,而另一個版本裡則沒有。
這一張是西元五世紀的《亞歷山大古抄本》[13],同樣未見這幾個字。“P74手稿”[14]是一份紙莎草紙[15]抄本。很多人可能認為紙莎草紙更早期一些。不一定,它比古書手抄本出現的要晚一些。它來自於西元七世紀,同樣沒有這幾個字。
這裡引用了兩位最偉大的新約學者奧曼森和梅茨格[16]的話,他們寫了一本名為《希臘文新約文本指南》[17]的書。布魯斯·梅茨格是聖經新約研究領域的傳奇人物,他們這樣寫道:“這段內容,”就是指希臘文“無需遵行這事”這六個字(英文則是八個),“它是對於雅各裁決原意的西方式解讀。”這很有意思,這些人知道你們不需要遵行妥拉,這就是他們的出發點。如果把這六個字插入到上下文裡,他們同意這六個字是被添加的,那麼他們是在解釋雅各原本的意思(他們以為的),即這就是雅各想說卻沒有說的話。西方的某個作者,西方的羅馬帝國,這個西式的解釋就是加上這八個英文詞(希臘文是六個字),目的是告訴你,以免有人讀了雅各的話,以為要遵行妥拉。所以他們加上這幾個字,讓雅各的意思變得更加清楚,“無需遵行此事”。
五、徒21: 25帶來的思維範式
這個例子最精彩的地方在於,它不是關於翻譯技術上的差異問題,而是我們該相信哪份手稿的問題。新修訂標準版(NRSV)聖經翻譯,並不是從聖經中刪除了這六個字,它們只是根據不同的手稿翻譯的。
如果邁克跑來說:“不是我要從聖經中刪去《約翰福音》六章4節,而是我以一份手稿為依據得出這節經文原本不存在的結論。”那我想我們可以談談。如果他只是單純地從聖經裡抹去一些字,那人豈不是可以任意刪減聖經?任何你不喜歡的經文,刪掉它們就是了。但如果他有一份確實的文本,那我們就可以認真討論一下。
說到這裡,現在我想來談談《約翰福音》六章4節。看看我們目前都掌握了什麼,有什麼證據嗎?因為有一段文字,在一份手稿(或文獻)中,有證據顯明,邁克的說法決不是出於“我不喜歡這段經文”或者“它不符合我的理念”的理由。
【約】以及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敢於超越我們眼前所看到的版本。
【尼】請告訴我們你和朋友最後怎麼結束這個話題的。
【約】很遺憾,我們最終意見未能達成一致。我問他,你的版本是這樣寫的,而我的版本則不同,我們來仔細研究一下文本內容吧。他卻回答說,我沒必要那樣做。我說:“一個版本是有啟示的,而另一個則沒有,那麼到底哪一個才是領受了啟示的版本呢?他說:“是英王欽定版(KJV)”我說:“好吧,英王欽定版(KJV)在出版的第一年,就被修訂了好幾次呢。”
【尼】咱倆其實一起去過聖經博物館的,快和他們講講。
【約】我手機裡正好有一張,在英王欽定版聖經展覽館裡拍的照片。那裡有許多不同版本的英王欽定版聖經,最上面的橫幅寫著,“150年間的不同修訂本”。後來我就給我朋友發了這張聖經博物館的照片,直到最後,他的答案仍然是:“以我手中的版本為准。”
展覽館中甚至有一部印刷版的英王欽定版聖經,以其惡意的內容而著稱,是印刷錯誤,上面印著“你們應該犯姦淫”,感謝上帝我朋友手裡的可不是這本。
【尼】我一定要得到這個版本,我怎樣才能得到這個版本呢?
【邁】尼希米,您曾在聖經博物館裡待過一段時間,那些來自世界各地,具有幾百年歷史的卷軸都經過您的手。
【尼】對。實際上,聖經博物館擁有世界上最重要的藏品,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妥拉卷收藏。他們讓我和約翰一起進入保險庫,檢查一些手稿。我們在新約中討論的內容,我們在舊約(即塔納赫)中也看到了。查看這些不同的妥拉卷,並且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沒有一本書的手稿完全相同。人們研究凱撒大帝[18]的著作,他入侵了英國,並且橫渡盧比孔河。我們查看了那些手稿,沒有兩份是完全相同的。
現在,你們可能會想:根據那些記述凱撒大帝的文獻,我們準確地瞭解到古羅馬時期發生的事情。可事實上,我們瞭解發生在凱撒大帝身上的事情,遠少於我們所瞭解的聖經新約。聖經新約的文獻紀錄被認為是古代世界文獻中紀錄最好的書。我認為新約聖經的見證人比現存的任何一本書都多,甚至可能比塔納赫(《希伯來聖經》)還要多。因為關於它的手稿更多。
這些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如果今天我們去印刷一本書,我們會怎麼做?我們會先建個PDF文檔,然後會製作與那份PDF文檔相同的副本。在古代,人們怎麼做?比如保羅給帖撒羅尼迦教會寫了一封信;後來有人造訪帖撒羅尼迦教會,並且複製了這封信,假如他們把這封信帶回哥林多;再後來,又有人到訪哥林多教會,他們會說:,“哇,保羅寫給你們的信真寶貴啊!”然後他們就會複製這封信。這些書信就是這樣在基督徒當中傳播開來的。正因為如此,有時候一些錯誤也會被複製;但另一方面,正確的版本也會被複製下來。
有時你會看到成千上萬份手稿,發現在那幾千份手稿中都有那個錯誤,而只有一小部分保有正確的內容。這就是《使徒行傳》二十一章25節的例子。這六個被添加上去的字,除了惟以英王欽定版(KJV)為權威的人以外,所有人都同意它們是被後來添加的。世界上任何一位嚴謹的學者都同意它們是被添加的。
這六個字出現在絕大多數的新約手稿中,它們在拜占庭文本[19]中也有出現。如果你做個統計就會發現,在該例中有很大一部分選擇加添這幾個字,只有相對較少的一部分早期手稿保有最初的解讀,沒有加添這些字。所以,你不能只是根據多數的手稿判斷,你不能總是因為它們是最早期的手稿就盲目跟從,你必須看看證據是什麼,看看有什麼證據支持某件事。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對《約翰福音》六章4節所做的。
不過,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有人從這裡回去以後說:“哦,我再也不能相信我的聖經了。”事實上,我從這項研究中收穫的重點是,新約的文獻資料令人震驚。當你把它和任何其它古代文獻進行比較時,我們有更多證據支持希臘文而不是別的。我曾和約翰談過此事,我說:“當我說到《比較希伯來文與希臘文中的耶穌》時,我提到一點,別扔掉你的希臘文聖經。我是說,希伯來文是原文的另一個見證,但希臘文仍然是主要文本。”因為希臘文仍然是主要的見證,它不能被忽略。
現在我們來看《約翰福音》六章4節,邁克,於我而言,在我們找到確實的書面證據以前,有個問題我們必須先來解決,究竟是什麼讓你認為約6: 4最初並不在聖經裡?
六、約6: 4爭議的福音書事件背景
【邁】問得好。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張圖表(見下頁)。當然你們無法看到所有的內容,但我要在其中一些地方做些說明,這非常重要。
這一天就是耶穌接受洗禮的日子,《馬太福音》、《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都提到祂在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法利賽人也在同一天,差利未人和祭司去施洗約翰那裡問他:“你是那位彌賽亞嗎?是將要來的‘那先知’嗎?”這是在耶穌受魔鬼的試探那天發生的事。
接下來第二天,耶穌便從曠野出來,這裡是約翰福音的內容。《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均停在耶穌四十天受試探這裡。《約翰福音》接棒下面的內容。耶穌去參加了逾越節。逾越節以後,祂繼續待在耶路撒冷並給人施洗。
然後到了《約翰福音》四章1節。當耶穌發現法利賽人知道祂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時(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乃是祂的門徒施洗),就在那時,耶穌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祂就離開了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
在耶路撒冷以北大約十八小時的路程中,遇見了井邊的撒瑪利亞婦人。耶穌在撒瑪利亞城中住了兩日,然後又回到迦拿,就是祂曾經變水為酒的地方。這都是在逾越節前夕。接下來,他就沒有時間去服事這個大臣,大臣的兒子快要病死了,耶穌對大臣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第二天在大臣回去的路上,他聽到他兒子已經痊癒的消息。
隨後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幾天之後,耶穌於星期五到了耶路撒冷。祂於次日安息日這一天,醫治那個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也就是五旬節前的那個安息日。第二天是五旬節,有一大群人在聖殿山上。也就在這時,法利賽人商議要除滅耶穌。因為祂在安息日醫治病人。祂告訴那個人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這就違反了法利賽人的規條。那裡說耶穌在聖殿山,祂說:“約翰是點著的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也就是在那時,耶穌知道了,當祂還在加利利時,施洗約翰被抓進監牢了。
現在,《馬太福音》、《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都告訴我們,當耶穌知道施洗約翰被下在監牢裡時,祂就離開加利利並開始在會堂裡教導。這段就是祂在會堂教導的時間。第一個地點在拿撒勒,在那裡祂讀了以賽亞先知的預言,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這是在那一周結束的時候。因為那天是安息日,是第七天,這七日的頭一日是五旬節,開啟了神悅納人的禧年。這是從耶穌的服事事工來看,神悅納人的禧年從一個五旬節開始,到耶穌以聖靈為門徒施洗的這個五旬節為止。
這樣,我們看到約翰涵蓋了整條線索直到五旬節,然後是《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記錄祂訓練門徒並在六個月後差遣門徒,然後他們再重新聚集。當耶穌再次把他們重聚在加利利時,他們是一起來的,並且帶了一大群人。這裡就是耶穌喂飽五千人,還有婦女和孩子。
女士們,先生們,這裡是唯一一處四位原福音書作者都記載了的神跡。這正好給了我們一個時間點,四部福音書毫無差錯地擁有了同一個時間標記。你可以相互對照,所有內容都對的上,在所有福音書中關於耶穌服事的記載,沒有缺失任何一天,也沒有任何一周或者什麼事件是缺失的。這是七十個周的服事,從耶穌接受洗禮那天開始,到祂以聖靈為門徒施洗為止,總共四百九十天時間。
現在,你已經在腦子裡把這些內容和《但以理書》聯繫起來了。“七十個七“實際上是指70個周。第62周後,也就是過了62個七日,在第63周,就在這一周,從中間被打斷了。經過三天三夜在墳墓裡,耶穌在安息日這天從死裡復活了。然後在接下來的那天,也可以說是日落以後,這一天就是初熟節,從這一天起,我們開始數七日,也就是七個安息日。之前已經有62個七日了,在62個七日以後我們再數一個七日。我們在這個七日當中,然後我們再數7個安息日,這就將我們一路帶到耶穌服事的終點,就是門徒在五旬節接受聖靈的洗。
現在,我們遇到個問題,這四部記載了耶穌喂飽五千人的福音書中,出現了《約翰福音》六章4節。但是裡面有添加的字,“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這就是關鍵所在。女士們,先生們,我花了20年時間,努力讓福音書的記錄合理通順,但我卻沒法把它們理順。而我最不願意做的,就是從聖經裡刪掉一段經文。
如果“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這是在第六個月月末,《約翰福音》六章4節是逾越節,但《約翰福音》七章卻是住棚節,那麼我們就有整整半年的空白期,讓耶穌去了一個祂從沒去過的逾越節;然後又需要半年的空白期,讓耶穌回到祂去過的那個住棚節。《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住棚節[20],正是發生在五餅二魚的神跡之後,那麼“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這幾個字加進來是意欲何為呢?整整一年空白期,這就是整個動機。我不會說這動機到底是什麼。我們來讓早期的教父們,以及約翰的研究發現,我們請他來告訴大家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七、聖金口約翰對約6: 4的謬誤解釋
【尼】太棒了,邁克,這樣我們就能明白了,您對於“《約翰福音》六章4節是添加的”之解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所謂的詮釋範疇[21]。如果把《約翰福音》六章4節刪除,那麼福音書內容的時間順序,從您的解釋來看就會合理得多。如同我從一開始說的那樣,我不能斷定《約翰福音》六章4節是否是後來加添的,我所能做的就是為你們提供證據。
對我來說有意思的是,優西比烏[22]是如何相信耶穌的服事期為三年半?我們來看一段摘錄。儘管優西比烏承認《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只記錄了一年時間。這是他在《教會史》(Church History)[23]一書寫下的內容。優西比烏生活在西元4世紀,他是君士坦丁時期的宮廷史學家,他寫道:“因為很明顯,這三位福音作者,”就是指馬太、馬可和路加,“只記錄了施洗約翰入獄後一年裡耶穌所做的事,並在他們記錄的開頭就指出了這一點。”這就是在說,優西比烏所計算的其餘兩年半時間,必須得在施洗約翰入獄以前發生。
我們先來快速流覽一下關於節期。在《約翰福音》中總共提到六次節期,它們分別是:
- 《約翰福音》二章,當耶穌受洗時的逾越節;
- 《約翰福音》五章,一個未指明的節期;我們接下來會多次提到這個未指明的節期,約翰福音五章這裡說:“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但沒有明確指出這個節期是什麼。根據邁克的《編年體福音書》來看,這個節期應該是五旬節,待會我們再來看。
- 《約翰福音》六章4節寫了逾越節;
- 《約翰福音》七章是住棚節;
- 《約翰福音》十章是光明節,也就是修殿節;
- 當然,《約翰福音》十三章是最後一個逾越節。
如果沒有《約翰福音》六章4節混在其中,那麼你會看到,與其它三部福音書一樣,就結束了這個一年的週期。這裡有一個確切的週期:逾越節、五旬節、住棚節、修殿節,然後再一個逾越節結束那一年。約6: 4可以說是混在其中打破了這個週期。
不僅僅是邁克說:“這裡好像有點不對勁。”許多學者在近四百年間也提出了同樣的質疑。在我們討論那些以前,我想先來說說一位教父。這些教父們就是早期的基督教作家,我們稍後會解釋得更詳細些。
這個人名為聖金口約翰,他很討厭猶太人,尤其討厭在他那個時代有基督徒去猶太會堂。他認為他們正在變得猶太化,這令他火冒三丈。所以,他在評注《約翰福音》六章4節時,想解釋清楚這個問題:耶穌在加利利究竟做什麼?祂在逾越節時向北走……,不是應該向南走,去耶路撒冷嗎?連聖金口約翰這個既討厭猶太人、又討厭妥拉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他是這樣說的:“有人說:‘祂(耶穌)為什麼不上去過節呢?眾人都湧向耶路撒冷時,祂自己卻往加利利去了”——因為你需要上到耶路撒冷去過逾越節,耶路撒冷根本不在那個方向,“‘而且,不是獨自一人,還帶著門徒往迦百農去。’”如果你們瞭解地理,祂往迦百農去,也就是往東北方向,而耶路撒冷在西南方向,究竟是什麼原因令祂去往相反的方向呢?而且還帶了一群人和他同去?聖金口約翰給了我們答案:“因為從那以後,祂就暗暗地廢除了律法,從邪惡的猶太人當中解脫了。”這就是他的結論。因為從《約翰福音》六章4節來看,真得很不合理。
八十年代有部很有名的電影,也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部,我忘了它的名字,是約翰·坎迪主演的,他駕駛一輛車在一條雙向車道上,沿著錯誤的方向行駛著。正下坡時,有人在窗外朝他們大喊:“喂!你們走錯路了!”他轉過頭來對他朋友說:“他們怎麼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呢?”(觀眾大笑)但耶穌可是走錯路了,祂去北方而不是耶路撒冷朝聖,這完全不合理。
【邁】當耶穌到達迦百農時,那裡的會堂擠滿了人。
【尼】會堂裡擠滿了人,經上說大約有五千人。他們在城郊鄉下做什麼呢?他們本該都去耶路撒冷嘛。沒有供給就沒法一直站立,不是嗎?如果他們要上耶路撒冷去,一定會帶著食物,以便路上所需。可情況並不是這樣,耶穌卻提供他們食物,因為他們已經出來了一個下午,都出來聽耶穌講道。所以這裡一定有問題,這很重要。邁克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
【約】而且,這還不僅僅是時間不對的問題。對於所有基督徒而言,這裡都存在一個問題;這也不僅僅是耶穌是否只服事了一年的問題;也不是你們是否相信要遵行妥拉的問題,即便你相信隨著耶穌的受死、埋葬與復活,妥拉也被廢除了。
我和許多基督徒談過,他們當中有一些人相信,耶穌是故意違反了妥拉。但這些人是少數,大部分基督徒都明白耶穌一定是那個無瑕疵的羔羊,祂不可能干犯妥拉,而是作為完美的祭物被獻祭。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根據福音書記載來看,如果《約翰福音》六章4節原本就在福音書裡,我們就使得耶穌不僅違反了逾越節的誡命,而且還帶領很多人跟著祂這樣行,加入一大群不守逾越節的人當中。幾天以後,祂又出現在會堂裡,訓誨那些不守逾越節的人。這樣,你就要處理整個逾越節被藐視的問題,而耶穌正是這問題的中心。
第二章 早期教父有話說
一、編者概述
借助於非常先進的資料庫和檢索方式,尼希米團隊發現,邁克·儒德在《編年體福音書》中認為“《約翰福音》六章4節是添加的”之觀點,早在400年前就由一位名叫紮卡裡·皮爾斯(Zachary Pearce)的英國新教徒提出了。繼而他們又找到最早於1643年談論這節經文的荷蘭新教徒沃修斯(Gerhard Johan Vossius),其觀點所代表的時代共識,同樣認為最初文本裡沒有逾越節這一詞彙。
藉由沃修斯等人的論述,尼希米發現,早期基督教父所閱讀的聖經版本裡,也沒有這節經文。尼希米和約翰·拉凱爾對早期教父的研究和彙報,為我們打開一扇認知的大門,讓我們瞭解到教父對聖經原始文本的引述之多,僅從他們的引文,就足以構建整本新約聖經的全部內容。
第一位出場的教父是革利免。他根據路加福音引述以賽亞書的內容,認為耶穌服事的時間就是一年。第二位教父愛任紐對此持不同觀點。尼希米團隊並不在意教父之間的不同觀點,而是從這背後推導出他們所看到的、也就是那個時代的聖經文本,裡面是否包含《約翰福音》六章4節。
對第三位、也是三大教父之一的俄利根的觀點考證,是更為深入的。俄利根在亞歷山大城受過專業的文本鑒別訓練,他把所學之長應用於基督教文本領域,取得顯赫的成就和影響。因此,尼希米和約翰·拉凱爾引用俄利根的多本不同著作,對耶穌服事時間、以及是否多出《約翰福音》六章的逾越節,均作出了詳實的證據羅列。
最後,尼希米也鼓勵我們多瞭解不同的觀點,包括為三年半服事辯護的著名人物或書籍。這一類的代表,包括基督教史學奠基人優西比烏。這也讓我們看到在第四世紀時,關於《約翰福音》六章4節已經存在兩種不同的聖經版本。
二、四百年前新教徒的時代共識
【尼】這段語錄來自1777年,一位名叫紮卡裡·皮爾斯[24]的人(Zachary Pearce)。紮卡裡·皮爾斯不是一位妥拉教師,我想他應該是英國的一位新教徒。他說,“有些人認為,(《約翰福音》六章4節的)‘逾越節’是一個插入詞。’interpolation’(插入詞)是個花哨的詞,其意思是‘添加’,而且我認為整句話都是添加的。”因此他的話和邁克在《編年體福音書》裡說的一模一樣,這可不是邁克自己編造的,這個觀點在學者口中說了至少400年了。
正如我所說,紮卡裡·皮爾斯作為一名普通的新教徒,他在告訴大家,《約翰福音》六章4節是添加上去的。他為什麼認為這是添加的呢?理由有許多,但最主要的理由是,“福音書作者的記述裡,沒有談到耶穌出現在這裡的逾越節;然而,‘盡諸般的義’(太3:15)的祂,若不就近出現在(這裡所述的)逾越節上,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在座各位,我想告訴你們一個秘密:邁克說過紮卡裡在1777年說的話。邁克,您知道紮卡裡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嗎?
【邁】早知他說過,我就不用花費20年功夫苦心研究了,哪怕我只是才開始學習閱讀英文……
【尼】公平地說,我們是使用了非常先進的資料庫,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才有了這些發現的,我們只需要查詢這些資料庫就好。我不知道您能否快速發現紮卡裡·皮爾斯,我們是使用這些資料庫才發現這些資訊的。如果是在五年前,我不可能找到紮卡裡·皮爾斯,那是花費畢生精力才能做成的事情。我們使用非常複雜的檢索方式,查找這些資料庫。約翰光是登錄這些資料庫就花了不小代價。普通人在谷歌上搜不到這些,您必須登錄這些售價昂貴的資料庫;有時候就算付了錢還不行,您還必須獲得“學者通道”來搜索某一特定資料庫。而我們就把這些發掘出來了。
我們發現最早談論《約翰福音》六章4節的基督徒,名叫格哈德·約翰·沃修斯[25]。他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新教徒,在1643年寫了一本書。我們把這本書帶到了現場,我給大家看看這本書。他是第一個提到這個的人,這是一本精美的書,這是最早的1643年版本。邁克,我們要把它作為禮物送給您。
【邁】噢,天啊!
【尼】在贈送禮物之前,我想先讀幾句作者的話,然後說說這本書是如何幾經輾轉才到我們手上的。首先,它是用拉丁語寫的,我們要把這段話翻譯過來。之所以能找到這段話,是因為我們在搜索資料庫時,裡面說最早提到這個的人是格哈德·沃修斯。
1643年他寫道:(也是邁克說過的)“……《約翰福音》六章4節最初的經文是寫成:‘但是,猶太人的聖日快到了’,這一點我們毋庸贅言。”換句話說,在沃修斯的時代有一種普遍共識,認為“逾越節”這個字是後來添加到六章4節的。由於他們相信住棚節可能出現在第七章或接下來幾章,他們認為,加入“逾越節”這個詞來打破時間順序,是說不過去的。而沃修斯說,“我周圍的每個人都在說,《約翰福音》六章4節加添了兩個字,我能解釋這種的原因。”他說“這句話是指住棚節聖日……,“但是抄經士由於疏忽,寫成了逾越節”。這是1643年沃修斯的時代秉持的共識。
他說“先人們……”,這裡很重要,請大家注意,“先人們”是指早期的基督教作家或今日所稱的教父,我們稍後再解釋這個詞。“先人們似乎沒有在《約翰福音》六章讀到‘逾越節’這個字”——我們會證明給大家看,不只是“似乎”,而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們說基督傳道一年或一年多的時間。”邁克,他在這裡說一年多的時間,這也是您一直在教導的,他們在1643年就談論這件事情了。
為了獲得這本書,我在網上找到義大利的賣家。我給她寫郵件說我三月份會用到這本書,她說辦不到。當時是十一月份,她說不能幫我在三月份拿到這本書。因為必須先從佛羅倫斯獲取一份特殊許可證,必須趕幾個小時的路程到佛羅倫斯獲取許可,才能從歐盟出口這本書,因為它是1643年的物品。
我說,看樣子您是幫不到我。我就找了一個比利時的賣家,他說 DHL三四天就能給您送到。當時是十一月底,我收到時已到了二月份。因為被扣留在海關,理由是這是1643年的書,我們不能讓它離開歐盟,我就必須走完所有海關流程。在此,邁克,我希望您的圖書館收納這本書,因為您一直被人攻擊。我不知道您一直以來的教導存在多少是非爭議,但是這絕不是無中生有的輕率觀點,而是基督教學者們說了至少400年的觀點。
【邁】謝謝您!要是我當初學習拉丁文,而且去了阿姆斯特丹就好了[26]。我只要幹那一件事兒就行了。
【尼】好的,現在給大家看另一條資料。我們要來觸及實際性的問題——就是教父。您會聽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我們已經看到沃修斯說的,他提到,教父們所知道的文本裡並沒有那個字,先人們沒有讀到“逾越節”那個字。亨利·布朗[27]是一名學者,1844年,作為基督徒的他,苦心研究耶穌生平年表。他寫道“儘管我相信在所有手稿版本中,均發現了約6: 4,但是在第一第二世紀的抄本裡不可能找到它。”
也就是說基督教的最初兩個世紀,正如我們之前談的,當人們去帖撒羅尼迦的時候,抄寫《帖撒羅尼迦書信》,然後帶回自己的地方。他們也是這樣抄寫《約翰福音》的。他說在第一、二世紀,《約翰福音》六章4節的“逾越節”一詞不可能出現在文本中。他真正的意思是,當我們研究教父,發現他們也不知道這個詞。我們將告訴大家他這麼說的理由。
在這之前我想先剖析這句話“我相信在所有手稿中……均發現了約6: 4”。這是亨利·布朗1844年說的話,我們通過數百個小時的研究,我們四個人——約翰和我,還有一個希臘的夥伴,還有“丁骨”先生,我們所有人查考不同資料,發現所有手稿均支持他說的話:約6: 4就在那裡。早期教父們不知道這一點,即流傳下來的所有手稿裡都有約6: 4,但我們發現這不是真的。邁克在他的《編年體福音書》略微提到兩份手稿,我們晚點兒再細談。
我不禁想到這些學者們是否有機會閱讀我們今天能查閱的手稿,若是有機會,他們會怎麼理解這件事呢?即使沒有機會閱讀所有手稿,他們依然深信《約翰福音》6: 4裡添加了這些字。我們來談談早期教父們。
約翰,您花了數百個小時,相當於讀了一個學士學位,來研究早期教父這樣一個課題。您說因為做這個研究,自己的生命被更新了,給我們分享一下吧!
【約】好的。邁克,當您最初發表《編年體福音書》手稿版時,我買了好幾份,當標準版出來時,我買了好幾箱分發出去。我認為那是最令人感興趣的編年體,我花了許多時間與人討論這本書。
早期教父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話題,首先我們得明白教父的定義。文字作品流傳下來的許多早期基督教作者,他們當中許多人被稱作教會之父或天主教會之父,他們並不都是天主教徒。我們今天將要引述的許多資料,被天主教會視作異端資料。他們一些人是官方認定的教父,有一些則不是。但我們可以通過教父來瞭解早期福音書的文本。
我們剛才在螢幕上展出的文本,阿提卡[28]、梵蒂岡這些,是三世紀及以後的文本。這些都是約翰和路加文本的複抄本的複抄本的複抄本的複抄本……。我們沒有原始文本,但是有一種途徑能讓我們接近原始文本,就是第一、二世紀著名基督教作者的文稿。他們引述和評述了原始文本的內容。所以通過閱讀這些教父們最古老的著作文稿,我們就知道其背後的原始文本是什麼。
三、早期教父對聖經原始文本的引文貢獻
【尼】這裡我想強調一點。當您聽到教父(教會之父)這個詞的時候,它不是指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他們是新約聖經的作者。認識這些作者的人們,有時被稱為“使徒教父”[29];認識使徒教父的人們,被稱作“教會之父”(教父),有時教父是這些使徒的門徒。當我們言及教父時不是在說,噢他們是教父的父親,我們必須聽他們的。我們在座的三位講員都不認為,教父是像福音書作者一樣受聖靈所感的作者。
教父之重要性在於,他們見證了早期的新約文本的內容,他們都讀過新約……。我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不在於教父們如何理解這些新約經文——他們的解經固然有意義,但我真正感興趣的是他眼前的福音書文本。因為我們都沒有原始文本,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閱讀教父的著作,在某些情況下再現和復原原始文本。
約翰,您這邊有一段精彩引述,來自梅茨格[30]和埃爾曼[31]合著《新約文本》[32]一書,這是大學課程的權威著作,來給我們讀一讀他們怎樣描述教父的吧。裡面有關於“引文”的描寫,引文是指教父逐字逐句地引述新約,他們是怎麼描寫“引文”的呢?
【約】他們對新約有“超過一百萬次的引文”。“這些引文如此廣泛,以致於即便我們所知道的其它所有新約文本資料都被毀掉,它們也足以重建整個新約文本。”
【尼】這太重要了,如果我們連一份新約初始手稿都沒有,只有教父的著作,我們就能重現新約裡面的內容,因為他們逐字逐句引述太多次了。順便一說,我們在對猶太聖賢的研究中也使用同一方法。這些都是專業詞彙,教父是指從二世紀到大約七八世紀的基督教作者;聖賢(Chazal/Sages)是猶太人的專業詞彙,指《米書拿》《塔木德》《托塞夫塔》[33]《米德拉什》等著作,是某一特定時期的著述。由於我們沒有二三世紀的舊約《塔納赫》[34]原始手稿,我們固然擁有死海古卷,但最初如果想知道原始手稿裡是什麼內容,就要去看拉比們的引文和如何引述的。那麼,這樣做總是有一點風險的。
我們舉例早期拉比的著作《米書拿》,看看它是如何引述(書面)妥拉的。由於我們沒有西元200年的《米書拿》抄本,我們只有1000年後的抄本。在抄寫的過程中,有時候會發生一件事,他們會更新裡面的內容。比如,抄寫員會說,利未記可不是這麼說的,我要依照每週妥拉誦讀的內容,來相應改寫這裡面的內容。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教父身上,甚至在《約翰福音》六章4節,我們沒有時間詳細講解這個。但是學者們相信,約6: 4是後來的抄寫員按照他們的理解,按照所相信應該發生的,加添到了教父的著述裡。我們要看幾條確切無疑的資訊。首先我想說說教父革利免[35],約翰,您來給我們講講革利免吧。
1、教父革利免
【約】好的,革利免生活在大約150至215年間。他是一位作家,在亞歷山大教導學院[36]任教。亞歷山大[37]是著名的聖經研習地,也是古代最大的圖書館所在地。革利免死在耶路撒冷,門徒眾多,後來成為著名人物的俄利根[38]就出自他門下。革利免寫的書有一本名叫《雜記》(Stromata)[39],基本意思是“混雜的”,是一整套各個方面的教導。在他的教導中,他提到耶穌服事的期限。
【尼】我們能看看他是怎麼說的嗎?再次強調,我們不是要瞭解革利免的觀點,而是想知道他看到過的《約翰福音》是哪個版本,裡面是否有約6: 4。我們已經看到像紮卡裡·皮爾斯和亨利·布朗這樣的學者,均相信福音書裡沒有約6: 4。
“耶穌到了受浸的時候,大約是30歲……”,他在解析那節經文,“祂傳道的時間必然只是一年,聖經同樣也寫了:祂差我宣告耶和華悅納人的恩年[40]……”這也是邁克的《編年體福音書》的副標題,是引述了《以賽亞書》的經文。 “先知書和福音書都說了這句話。”換句話說,他讀了福音書,他說福音書裡寫的明明白白、十分清楚,耶穌的服事時間是一年。它說了耶和華悅納人的恩年,就是指耶穌的服事。為了瞭解上下文,這裡經文來自《路加福音》4: 16-19,引述了《以賽亞書》6: 11-2,“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41]
根據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所說,它的意思就是指耶穌的服事是一年時間。要記得,甚至優西比烏也認為,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都是一年,因為他們的講述聽起來就像一年時間。儘管優西比烏擁護三年半的服事時間,但他認為前三本福音書裡只有一年時間。革利免說,是的,耶穌的服事就是一年。那麼,亨利·布朗……噢,約翰,您說。
【約】這表示說《編年體福音書》裡的觀點,不是什麼標新立異的觀點,而是在一世紀末二世紀初就被教導過的。一直到三世紀,這是最古老的有文獻記載的觀點。《編年體福音書》並沒有標新立異,這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學院和最著名的人物提出來的觀點,是那所學院所教導的觀點。
【尼】因此,邁克的觀點其實已被教導一千八九百年了。邁克,你準備好改信天主教、接受教皇的領導嗎?(現場觀眾笑)
好,我們引述過亨利·布朗的話,在1844年他寫道:“儘管我相信在所有手稿版本,均發現了約6:4,但是在第一第二世紀的抄本裡不可能找到它。”我前面分享過這段話,現在您知道他的意思了吧。我們和他一樣都在查證革利免的話,他提到了革利免。但我沒那麼聰明,儘管我原封不動複述亨利·布朗的話,但我要究其根源,而非馬上相信亨利·布朗說的。我想親自看看革利免是怎麼說的。我把革利免的話發送到希臘那邊,找人求證其翻譯準確性,來核實這件事。而亨利·布朗說的話被證實了——在大約西元200年,革利免的著作中,裡面沒有提到《約翰福音》六章4節。否則,他怎麼可能說耶穌的服事是一年呢?不可能啊!他至少會說兩年以上的時間。
【邁】嗯,在《約翰福音》2章3章是第一次逾越節,《約翰福音》12章是最後一次逾越節。如果他們的福音書裡有《約翰福音》6: 4,這些教父和學者就不可能愚蠢到不知道,必須需要兩年以上時間才能過完三個逾越節。我在序言中說過這句話,現在您證明了它的正確性。
【尼】我們只是拿出實際的引文,您們可以自己查看。您自己來決定,並不需要依賴邁克說的話,您可以直接認同革利免、邁克、紮卡裡·皮爾斯,亨利·布朗和其他這麼說的人,您看 還有其他的觀點。
【邁】還有沃修斯,
【尼】沃修斯相信的是超過一年,他直接忽視了那句經文,他直接忽略那句話,但他提到,那是他那個時代的一種共識,這是沃修斯的貢獻所在,那麼……約翰,您有要補充的嗎?
【約】還好。只是在這種情況下,您沒必要同意革利免的觀點,記住這一點很重要。我和別人討論過這個,所以您現在相信教父們寫的一切話嗎?
【尼】不!
【約】你要改信天主教嗎?我生下來是天主教徒,從小就受洗了,我不會回到天主教的。我們甚至不必同意革利免的觀點。在對革利免的這段引述裡,他表述了自己的觀點,是他從福音書中梳理出的結論。如果您認為當時世界最著名學院的最著名教師,會忽略福音書中那節直白簡單的經文,則是有些牽強附會了。當然,我們知道有一些著名教師,會忽略聖經中直白簡單的語言(現場觀眾笑)。所以我們不止需要革利免的觀點——,
2、教父愛任紐
【約】我們查考教父資料,發現了愛任紐[42],他的觀點略有不同,他有不同的嚴謹結論。
【尼】給我們說說里昂的愛任紐吧。
【約】他生活在130-202年間,是坡旅甲[43]的門徒,據說坡旅甲是使徒約翰的門徒,因此愛任紐是使徒約翰(福音書作者)的隔代門徒。愛任紐是二世紀的異端捕獵者,他把異端列舉在自己著作裡,然後抨擊它們。
【尼】他寫了本書叫《反異端》,那邊書的原標題是什麼?
【約】《對靈知(Gnosis)的揭露和摒棄》
【尼】這就是我們正在談論的諾斯底主義(Gnostism)[44]。
【約】他的寫作主要是反駁諾斯底主義。他對耶穌服事的時間有自己的看法,依據他對《約翰福音》八章57節的解讀,是關於亞伯拉罕的經文。他們對耶穌說,你還沒有五十歲,怎會見過亞伯拉罕呢?愛任紐讀到那句經文,認為他們不可能對一位30歲的人那樣說話,所以祂至少也有40歲了,也許當時快50歲了,所以愛任紐認為耶穌的服事時間是20年。
【邁】【尼】20年服事時間?!
【約】我們關注的不是愛任紐的觀點,我們關注他是因為他知道這一觀點的長期存在,即耶穌一年服事時間的主流教導。他就向持守這種教導的一位教師發起了論戰,他說,我要證明諾斯底主義是多麼的淺薄,他說:“讓我們回到福音書記載裡,數一下逾越節的次數,我們可以證明祂的服事不是一年。”
【尼】更清楚一點的說,愛任紐是反對一年服事時間的,他想證明服事的時間不止一年,所以他想數算自己知道的每一個逾越節,來挑戰瓦倫丁主義[45],以證明它一年服事時間的觀點是錯的。
【邁】接受挑戰!
【尼】好,他說:“令人驚訝地是,瓦倫丁主義者和邁克·儒德(現場觀眾笑)[46],自稱發現了神的奧秘,卻沒有查看福音書裡主受洗後去了幾次耶路撒冷,並在那裡慶祝逾越節……”接下來他開始講述他所知道的幾次逾越節,我們關注的不是他的觀點,而是他讀到的《約翰福音》是什麼版本。“祂第一次上去過逾越節,是在約翰福音二章迦南婚宴使水變酒之後……那次之後,祂又一次上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那時祂醫治了水池邊躺了38年的瘸子,是在約翰福音五章……”我們稍後再說這一章,那是第二次逾越節,約翰福音二章、五章,“……祂再次起身去提比哩亞湖的另一邊,”他這裡說的是《約翰福音》六章,沒有談到逾越節。
他想告訴人們的是,耶穌上到耶路撒冷,又離開耶路撒冷;上到耶路撒冷,又離開耶路撒冷;祂每上去一次都是一年。《約翰福音》六章被他引述,作為離開祂耶路撒冷的證據,而沒有提到任何逾越節的字句,“……祂再次起身去提比哩亞湖的另一邊,一大群人跟著祂,祂用五餅二魚喂飽了所有人……然後經文寫道,逾越節前六天祂來到伯大尼(約十二章),祂從伯大尼上到耶路撒冷,吃了逾越節筵席[47](約十三章),第二天受難(約十九章),任何人都會承認說,這三次逾越節不可能發生在同一年。”愛任紐的三次逾越節是哪三次呢?《約翰福音》二章,《約翰福音》五章中未指明的節期,以及《約翰福音》十三章最後一次逾越節。他為何沒有提到《約翰福音》六章4節呢?
【邁】《約翰福音》二、三章是逾越節。祂上到加利利湖,在撒瑪利亞村莊停留,然後去迦南,把水變成酒,然後祂在《約翰福音》五章再次回來過逾越節。(按照愛任紐的邏輯)這就是接續發生的事:《約翰福音》二、三章是逾越節,《約翰福音》五章也是逾越節?太蠢了,不,《約翰福音》五章是七七節,是逾越節之後的下一個節期。
【尼】有道理,我不確定,對我而言重要的地方是,不管他笨不笨,他看到的聖經版本是沒有約6: 4。因為如果有,他不可能不提到。
【約】如果《約翰福音》6: 4在他的聖經版本中,那他就是實實在在的笨蛋了。
【尼】沒錯(現場觀眾笑)。所以我們不再糾結於約6: 4是否是初始經文,我們開始決定愛任紐是不是個笨蛋了(現場觀眾笑)。
【約】如果說他的聖經版本有約6: 4,就是耶穌三年半服事時間的論據的話,愛任紐也是個笨蛋。
【尼】好吧(觀眾笑),這是他們說的,不是我說的。
1844年,亨利·布朗作為一位新教徒教師,正致力於編年體的研究……這不是我臆想出來的,是我通過查考使用手中的資料得出來的。如果使用傳統的研究方法,這會是一個三四十年的大工程,而且無法獲得全面的資訊,但是我有機會進入這些資料庫裡。亨利·布朗寫道:“毫無疑問,我認為聖愛任紐,沒有讀到《約翰福音》6:4逾越節的字詞。既然他在《約翰福音》5:1節,如此渴望在不是逾越節的地方找出逾越節,他就不可能錯過任何一節提到逾越節的經文,尤其當他明明讀到那節經文的時候……”他提到,《約翰福音》六章是耶穌離開耶路撒冷的例子,而不是來耶路撒冷過逾越節。所以,您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愛任紐和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一樣,在西元200年讀了《約翰福音》,而且在他們讀到的福音書裡沒有約6: 4!
3、教父俄利根
我們將要講述的三大教父的第三位(儘管不止三位,但時間不允許我們全部講完),叫俄利根(Origen)[48],這個詞的末尾是E-N,所以不是Origin(起源),表示希臘語裡的Oreginus。給我們講講俄利根吧,他是一位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人物。
【約】他是革利免的門徒,革利免提拔他為亞歷山大教導學院的院長。俄利根年輕時就對神的話語感興趣,他的父親里昂達斯是一位殉道者。他本想和父親一同去殉道,他母親用衣服把他藏了起來,這樣他就不會落入外面的異教兵丁之手。當他父親在監獄的時候,他去探監,告訴父親:“無論如何,不要背棄信仰”。
他在年少時就願意服事神,一生中多數時間睡在地板上,禁食、吃素,不做任何分心事,專注於研究福音書。不論您是否同意他的觀點,他對神的話語卻是很認真的,從很小的時候就在認真學習。他最終如願成為一名殉道者,他在德西烏斯迫害[49]中遭受酷刑,不幸的是,他死於酷刑之傷。
有一件事情是與我們的談話相關聯的,就是俄利根受教於亞歷山大城,那裡有古代世界最大的圖書館。之前您提到“多種文本”的問題,不僅僅是新約基督教上的問題。我們有多種的文本,在亞歷山大城,他們有整所學院的人,致力於查究荷馬[50]創作的最初文本是什麼。因為人們手中的只是各種複抄本,有些地方彼此矛盾。
因此,俄利根學習了非宗教領域的文本批評[51],來恢復古代文本的初始語言。作為基督徒,他研究原始文本的各種複抄本,他把這項知識運用到了基督教文本領域。不僅是基督教文本,還有希伯來文本,自古以來他算是一位多產的基督教作家。哪怕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也是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他寫了一本書《六文本合參》[52]。
【尼】《六文本合參》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在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希伯來聖經的參考書。俄利根閱讀了《希伯來聖經》和希臘語譯本《七十士譯本》[53],他發現《七十士譯本》的不同手稿間存在互相矛盾。此外,拿《七十士譯本》與希伯來文本對比的話,他發現經文並不總是一樣,《七十士譯本》的經文有些沒出現在希伯來文本裡,反之亦然。
因此他創作了這本書叫《六文本合參》,分列六欄。第一欄是希伯來語,第二欄是把希伯來語寫成希臘語,他們把它抄寫為希臘語,第三欄是《七十士譯本》,四五六欄是其它希臘語翻譯版本,他以此對照每一個不同版本,在有差異的地方他標上注釋。我們一會兒再看他的注釋,這對於今天整場的分享非常關鍵。
俄利根的重要性在於,他生活在大約184至253年,他絕不盲從接受任何手中的文本。您之前談到您的朋友,他在探究之後仍只接受KJV版,因為手上拿到的就是這個版本,俄利根不是那樣子的人。恰恰相反,他到處獵尋手抄本,搜索不同文獻,作系統性對比。
在希臘文獻的研究中,人們把荷馬的著作當做神聖文本來研究,因此他們發明了這種系統的科學方法,用以對比希臘悲劇、荷馬著作和不同文獻,在對比中確認哪個是最準確的版本。俄利根說,我們不可以用同樣的方法研究聖經嗎?他就用這種方法研究了《希伯來聖經》和《新約》。在某種意義上,他是新約文本批評之父。文本批評是比對手稿的一整套科學。
【約】他也被基督教會認作是寓意解經之父,這一點很重要。而且與我們的討論相關的是,俄利根深刻認同,如果進行寓意解經,極其重要的一點是原始字句的準確性,否則解出來的寓意就會出現偏差。因此俄利根搜集了所有不同的抄本,勤奮地研究不同類型的抄本,來確保他獲得正確的文本。
【尼】這一點太重要了!如果您要把聖經中的某件事,象徵性和比喻性地解釋為將來美好事的影兒,首先您需要明白它字句上的含義。我經常看到人們身上發生本末倒置的現象,人們根據耶穌做的某件事的象徵性含義,去改變字面文本,讓它去表達那個意思,這樣就錯失了正確解經的機會。因為不瞭解字面意思,就不曉得象徵意義。俄利根在其著作《論首要原理》[54]中說:“……耶穌教導的時間只有一年零幾個月……”應該說,俄利根是讀了邁克·儒德的《編年體福音書》(觀眾大笑)……不!您看,這是教父們的普遍觀點。
【約】主流觀點。
【尼】是的,至少在最初幾個世紀來說是主流觀點。正如他的老師革利免所說,他們教導同樣的觀點。我們只有他關於《路加福音》4: 19的引文,而路4: 19講的是耶穌在拿撒勒會堂宣讀以賽亞書。俄利根寫道:“依照文本的直白意思……”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俄利根是位寓意解經家,寓意是指您可以把一件事解釋成任何事,不是嗎?但是他卻說,文本的直白意思。他在這篇《佈道》後文提到寓意,“依照文本的直白意思,有人說救贖主在猶太地傳道僅僅一年,這就是‘耶和華悅納人的恩年’之經文原意”(賽61: 2)。
如果約6: 4原本存在於《約翰福音》,有第三次逾越節的話,俄利根就不可能作出這樣的聲明,耶穌的服事就不可能只是一年,至少也得是兩年。
【約】俄利根對《約翰福音》整本書逐句寫了評述,然而,《約翰福音》六章被毀了,那部分的手稿遺失了,我們無法獲知,因此我們只能去看看最相近的,他對《約翰福音》五章無名節期的評注……
【尼】好的,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對約六章的觀點。他對約五章評論道:“對於那些聲稱約五章無名節期是逾越節的人,我們必須如此回應……”我們已經講過了,比如愛任紐就是持這種觀點,因此俄利根在回應持有類似觀點的人,“對於那些聲稱約五章無名節期是逾越節的人,我們必須如此回應:‘當祂在約二章來到加利利時,正好在逾越節前,之前,祂使水變成酒。在這些事後,是約五章的猶太人的節期。耶穌上到耶路撒冷,那時祂醫治瘸腿的。但如果約五章的無名節期是逾越節的話,事件的發生就會極其局促……因為會有太多的事件發生在約五章,來促成一次的逾越節,尤其是《約翰福音》七章提到住棚節近了。”
根據俄利根對約五的評述,我們不可在約二章和七章之間的第五章插入一次逾越節,因為二章是逾越節,七章是住棚節,若在五章加入一次逾越節的話,會讓事件的發生變得極其局促。如果不可能在五章塞進去一次逾越節,當然也不能在六章塞進去一次逾越節。自然,約6: 4也不能是逾越節,否則,事件順序就超級擁擠了。所以,即便看不到俄利根對約6: 4的評述,我們可以根據他對約二、五、七章的評述,推導出約六章沒有逾越節。
五、關於約6: 4存在不同的聖經版本
再次強調,我不在乎俄利根的觀點是什麼。我試圖瞭解的是,他眼前的《約翰福音》文本是什麼。當我們讀到亨利·布朗和紮卡裡·皮爾斯說,約6: 4是添加的,因為古代教父們沒有讀到這些經文,他們指的是亞歷山大城的革利免、愛任紐和俄利根以及其它人,我們無法一一列舉。我想再談一位認同一年服事的教父,這樣的教父太多了,不可能一一列出。
約翰非常謙卑,他給我發了封郵件說,您有空讀讀這本書,他發給我一篇250頁的論文(觀眾笑),是他前一天剛讀過的博士論文。我們只是在研究俄利根而已,還沒談到主題呢,他就花了數百個小時查考無數的教父資料。家人們,這是對您們的一份邀請,邀請您去進行自己的研究,不要只閱讀那些持有一年服事論點的人,那些認為三年半服事的人,您也要去閱讀,聽聽他們的論據,看看雙方都是怎麼說的,然後自己決定。
我們討論過一本喬治·奧格(George Ogg)寫的書,書名是《耶穌服事的時間》[55]。這是一位持三年半觀點的學者寫的書,我們詳細研究了那本書。
我們再分享一位教父泰考尼斯[56]。他出現的時間是大約西元380年,他活在優西比烏[57]之後。優西比烏是三年半觀點的第一擁護人,泰考尼斯在優西比烏之後五六十年寫了一本書,在書中他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毫無疑問優西比烏的聖經版本是有約6: 4的。
我很喜歡泰考尼斯這段引文,因為他提到《馬太福音》23:2-3,耶穌說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泰考尼斯寫道:“……祂的這些教導(太23:2-3)只是針對接下來兩天嗎?因為兩天后祂就死了……但是祂如果從傳道一開始就講這些事,其有效性就會是一年了。”他認為,耶穌為何花費時間談論法利賽人坐在摩西位上呢?因為祂兩天之後就死了。祂說的一切話都會無關緊要。泰考尼斯的假設是,耶穌在服事期間教導的每件事,其重要性只存在於上十字架前,之後就從這世界抹去了。所以他的結論是,這些談論對之後的教會成長只具有象徵意義;而它的字面意思則隨著耶穌的死而歸於沉寂。
因為泰考尼斯認為耶穌的整個服事就是一年。所以從祂服事第一天算起,祂教導不要聽法利賽人說的話,因為他們坐在摩西的位上,不要聽他們的教導,這教導有效性也只是一年時間。在那一年中,祂應該教導些什麼,使它們在受難日之前發揮其效力呢?那麼,祂為何浪費時間談這些東西呢?泰考尼斯的結論是,這些話在其後具有寓意和象徵意義。但是這裡的重點在於,即便是在優西比烏之後,泰考尼斯閱讀的《約翰福音》手稿中沒有約6: 4的經文,因為他也認為耶穌服事的時間是一年。
接下來我們談論更長服事時間的資料,我們會談到優西比烏和其它認同三年半服事的資料。至少在優西比烏的聖經裡,毫無疑問有約6:4。但是我們在第一、二世紀的基督教裡,甚至在第四世紀的基督教裡,存在兩種版本的《約翰福音》:一種有約6: 4,一種沒有6: 4。這兩種版本聖經存續到第四世紀。當然,我們也能展出二世紀其他版本的聖經,依據革利免、愛任紐和俄利根,在他們的聖經版本中沒有約6: 4。這就像《使徒行傳》21:25,我們不是要從聖經刪去一節經文,我們談論的是兩種共存的版本。
您或許不知道存在兩種版本,因為無人告訴您,於是您以為您目前所擁有的就是唯一的版本,只能相信它!但現在,您有了更多版本,現在您要決定到底跟從和相信哪個版本了!或者等到您找到所有證據後,去讀讀Ogg的書,聽聽不同的觀點,然後再自己做決定吧!
【邁】謝謝您,尼希米!謝謝您,約翰!(觀眾掌聲)
《編年體福音書》現已翻譯成中文、西班牙語、法語和其它語言,尼希米對逾越節一詞的研究,將體現在每一種語言裡,包括最新的英文版;約翰和尼希米的工作內容也會加進來。
我們只有三個半小時的談話時間,無法全部包含全部內容,所以我們的節目是濃縮的。但我非常感謝這兩位學者,兩位誠實正直的人肩並肩承擔了這個任務。他們做成了我做不成的事兒:我願把福音書的原貌展示給大家,而他們兩位幫助我把最終結果提升到了新的標準,我謝謝他們的付出!
第三章 真相之旅:古文本領域裡的福爾摩斯探案
一、編者概述
教父俄利根認為耶穌的服事時間是一年多,但是持三年半理論的人通常引述俄利根作為最古老的資料,來論證耶穌的服事時間是三年半,依據是他對《但以理書》的評述。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是擁護三年半理論的第一人,身為俄利根的隔代門生,優西比烏將俄利根對《但以理書》之“七”為70年的解釋,改為7年。他因此提出了耶穌在復活前服事三年半,復活後又與門徒一起相處三年半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觀點。這種寓意式、先驗性地解讀《約翰福音》文本的方式,讓《約翰福音》五章和六章分別多出一次逾越節,是缺乏證據支持的。
為了獲得更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尼希米團隊將研究方向轉向最艱難、也是最有價值的聖經古文本研究。尼希米試圖以文本鑒別的科學嚴謹性,來探究《約翰福音》六章4節是否屬於聖經。這幾乎帶我們進入了一個看似眼花繚亂、卻層層遞進展開的聖經手稿的迷宮。若非具有福爾摩斯探案的精神,真的難以發現這裡的真相是什麼。僅就472號手稿裡是否包含《約翰福音》六章4節,其論述的深度,已為我們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聖經古文本認知領域。
本集重點講述了《新約聖經格雷斯版》(或稱《尼斯勒和奧倫德版》)裡的一處相關評注,其中,文本變體、手稿查詢編號、德文著作《Text and Textwerk》和蘭貝斯宮手稿等是我們理解的著重點。
二、“1776”的紀念意義
【約】尼希米,我覺得現在大家可能還都不太明白“1776”的重要性,以及你所鑄造的這枚一盎司純銀銀幣和這又有什麼關係。
【尼】我們已經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搜尋帶有耶和華名字全部母音的手稿。兩年前,我只找到5份含有全部母音的手稿,大部分手稿都缺失一個母音。當門戶打開之後,人們開始把手稿數位化,不到一年時間我們找到1000份這樣的手稿。到今天這場節目錄製為止,我們找到1776份帶有全部母音的手稿!(觀眾鼓掌、歡呼、號角聲響起)。
整個團隊工作很認真,“丁骨”先生迅速搜集到更多手稿。有一次他查考了300份手稿,才發現兩三份手稿裡帶有全部母音的。您也許會期待我們第一年找到1000份,第二年又找到1000份。不,有時事與願違。很多情況下我們查遍許多手稿仍然找不到帶有全部母音的,然後偶然間發現了一份,就這樣我們累計發現了1776份。
這裡的銀幣,是1640年丹麥國王鑄造的。原先的幣上面有耶和華的名字,這一枚是依據1640年發行的丹麥幣仿製。上面是丹麥國王克利斯蒂安四世[58]的象,有耶和華的名字和Iustus Iudex字樣,意思是“公義的審判者”,是來自聖經的片語。這實際上是《瑪拉基書》的應驗。瑪1: 11說:“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右圖為1640年原始丹麥幣,C4表示克利斯蒂安四世,右邊為幣的反面。)
當人們在大約西元前400年從瑪拉基口中聽到這句話時,我無法想像他們會知道在丹麥冰島——他們從未知曉的大洋彼岸會提說神的名字,耶和華會在那裡得榮耀。所以我把那枚1640年版硬幣看做是聖經預言的應驗,我將把它的正面仿製下來,在反面加上《瑪拉基書》的經文。這是很棒的見證方式,我聽到來自全球的人們見面後拿出這件複製品,講述《瑪拉基書》裡面的預言是如何應驗的。在預言發出後的兩千年,應驗在了丹麥,甚至整個歐洲。
美國最初建立的時候還沒有官方貨幣,他們用的標準貨幣叫西班牙銀元[59]。他們問,有沒有其它能被美國國庫接受的貨幣呢?因此,湯瑪斯·傑弗遜[60]受託提供一份報告,來鑒定所有貨幣。他在報告中明確提到了丹麥貨幣。這枚上面帶有耶和華名字的貨幣,是美國建國初官方接受的為數不多的幣種之一,當時正是1776年。
【邁】1776!所以我就逾越了自己的權柄,對丁骨先生說,“下個月逾越節之後,這枚銀幣才能到你手上。”
我們回到手稿的討論中。我們發現,沒有一份古希臘語手稿不說到,耶穌醫治了瘸腿38年的人,或者耶穌醫治了生來瞎眼的。雖然我們現在處理的是微小細節,但細節關乎聖經經文的一致性,關乎我們能否回到神的話語中,回到由聖靈感動、被聖人寫下的內容。亦或說,我們順從於被篡改、被插入、遺留給我們的內容。這正是這兩位紳士所做工作的價值,他們對我在真理發現方面的支持,我無以回報。
尼希米隨我到過45座城市。當我講述我對希伯來文《馬太福音》的必然推測時,我說,約瑟(Yosef)是瑪利亞(Miriam)的父親,而不是以利的兒子約瑟(Joseph),即《路加福音》中瑪利亞的丈夫;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約瑟(Yosef Ben Yaakov)是瑪利亞的父親。
尼希米每天晚上聽我講述這些,我們巡迴演講45座城市。幾年後的吹角節,他拿來了原始手稿——兩份最古老的希伯來文《馬太福音》手稿的照片,裡面包含了耶穌的正確家譜,是通過瑪利亞的父親約瑟(Yosef Ben Yaakov)延續而來。瑪利亞生了耶穌,才使得耶穌是被擄巴比倫以來第14代人,甚至希臘文也這麼說。但是希臘文只說出了13代,尼希米找到的希伯來文裡面是14代。這是我一直以來的教導,因為這是一個價值1萬美元的問題,由一位拉比在20年前向我提出的。
現在,尼希米繼續帶領我們餘下的旅程,來講述《約翰福音》……
三、耶穌服事“三年半”說法的由來
【尼】好的,我想重述一下邁克說的話,是很重要的一個點,在查考約6: 4時我們發現西元2世紀的一些手稿裡並沒有約6: 4。證據來自這些教父們,比如亞歷山大的革利免、里昂的愛任紐、俄利根,還有其他我們未能查考到的人。這是基督教學者們幾百年前就認同的東西,這是他們討論、辯論和認同的東西。
我們瞭解到的最早辯論發生在1643年。沒有任何新約手稿裡的文本變體[61]會提到說,“耶穌不是彌賽亞”!這樣的手稿是不存在的。也沒有任何新約手稿說,“耶穌沒有第三天死裡復活”,這樣的手稿也不存在。《希伯來聖經》[62]也是一樣。比如,有的《希伯來聖經》手稿會把耶和華說成Adonai(主),或把Adonai(主)說成耶和華,但是沒有任何《希伯來聖經》手稿,會說妥拉不是摩西寫的。任何手稿都承認是摩西寫了妥拉,神在西奈山向60萬以色列男人和其他許多婦女孩子顯現,並直接向他們講話。任何現存的聖經手稿都保存了這一紀錄,所以我們這裡談論的是更深入的細節。
這些細節對人們來說很重要,因為有助於瞭解事件的時間順序——邁克已經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而我一開始的問題是:邁克說對了嗎?我不需要去證明他是對的。這源自我說的“詮釋範疇”[63],他對福音書看似隨機混雜的事件,對所有細節和資訊進行了合理的解釋。已經有人這樣做了幾個世紀。第二世紀時有個人叫他提安[64],試圖把四福音書進行編年體編排。所以基督教學者做這件事已有很多個世紀。
1、俄利根的觀點
當邁克這樣做的時候,約6: 4與他的編排模式格格不入。我們現在就是在找支援或反對的證據。我們已經談了二世紀的教父俄利根,他認為耶穌的服事時間是一年。他還有一些其他的觀點,顯示出那個時候他的福音書裡沒有約6:4。支持三年半理論的人比如喬治·奧格(我們之前提過他的書,很不錯,亞馬遜有售),認為俄利根在早年持一年服事時間觀點,晚年持更長服事時間觀點,三年半或者可能(將近)三年服事時間。
【約】三年半理論支持者們會引述俄利根,作為三年半理論的最早淵源。
【尼】他們會說大約三年……,
【約】這很重要,因為他們自己也承認,很難找到更古老的淵源了。他們引述過薩迪斯的梅利托[65],但存在爭議,所以三年半理論的擁護者通常引述俄利根作為最古老的資料。這來自他對《但以理書》的論述。儘管他們推斷俄利根延長了服事時間,但俄利根並沒有駁斥自己起初的觀點。他們推斷的依據所引述俄利根的話裡,並沒有數算逾越節的次數,因此沒有理由認為他換了不同的聖經版本,只不過是對《但以理書》的寓意解經罷了。
【尼】是的。比如,我們講到二世紀的教父他提安,他寫了本《四福音和參》[66],在其中把四本福音書按照他認為的時間順序編排。他把約6: 4也加進去了,然而我們只找到《四福音和參》的阿拉伯語譯本,我尚未找到原作文本。重點是,每當我們發現二世紀資料時,這些資料總是存在爭議的,也許唯一例外是“紙莎草紙66”[67]和“紙莎草紙75”[68],我們稍後看。但是我們先從俄利根開始,《但以理書》9: 27。邁克,您能讀一下嗎?因為俄利根對它有所評注。
【邁】“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或譯: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
【尼】俄利根在他對《但以理書》的寓意解經裡,把“七”解釋成70年,他把這裡的“七”或“周”解釋成70年的週期。他說,70年的中間就是基督的死,前35年是耶穌生平直到祂死,後35年是從祂復活到聖殿被毀(於西元70年)。因此,他需要讓耶穌大概死在35歲時,或者,如果他認為聖殿被毀於西元68年,時間也不確定,那麼就要早兩年,讓耶穌大概死在33歲。
遺憾的是,我們無法找到俄利根寫的全部內容。據我們所知,存留下來的只有拉丁文,而我們盡全力卻無法找到全部的拉丁文本。我們搜查了整個資料庫,這是一個持續性的項目。今天的教導之後我們仍然會繼續研究,約翰的目標是在每一份現存抄本中查考約6:4存在與否。他希望大家聯繫他,他的郵箱地址是 John6four@gmail.com,他會繼續這個項目,我也會幫助他。我們想找到有多少份抄本有和沒有約6: 4。我們今天給大家分享的都是我們知道的,但我們的認識可能會發生改變。
【約】在希臘文和古拉丁文之外,還有存留下來的其它語言抄本,不只是希臘文抄本。
【尼】是,我們也許會發現其它語言版本的聖經裡面不存在約6: 4。我們已經找到一份,但今天暫不分享,時間不夠。俄利根對但9: 27的寓意解經把“七”分成70年,35年和35年。據此人們有充分理由推斷,他把耶穌服事理解為三年半。晚年時他還有另外一項陳述暗示這個觀點,在他晚年著作裡有所體現,因此他可能是第一個持三年半理論的人。而他已經是第二世紀的人,儘管不能百分之百確定,但根據我們的瞭解,大體如此。
2、優西比烏的觀點
我們認為毫無爭議持有三年半理論的第一人,是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他生活在大約西元260年至340年,他因尼西亞大公會議[69]而聞名於世,他是主講人之一,也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宮廷歷史學家,給我們講講優西比烏吧。
【約】優西比烏是眾所周知的人物,他是潘菲勒斯[70]的學生,潘菲勒斯是俄利根的學生,所以他是俄利根的門生的門生。潘菲勒斯的著述和俄利根對《但以理書》寓意解經有一定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利根死後,潘菲勒斯寫了《為俄利根辯護》[71]。這個系列後來由優西比烏接手完成,因為潘菲勒斯被人殺害了[72],因此優西比烏必須完成這個系列。在潘菲勒斯的《為俄利根辯護》中,他引述《論首要原理》[73]的一年服事觀點。因此俄利根的門生依然從他的寓意解經裡,汲取了“一年服事”理論,並且繼續著書寫作來支持這一觀點。
【尼】大家記得嗎,如果是一年服事理論,約6: 4就不可能出現在福音書裡。
【約】優西比烏的解釋(插圖見下頁)和俄利根的解釋是有關聯的。俄利根看到《但以理書》的“七”,他想把年份填充進去,從耶穌降生到聖殿被毀之間,他想分成兩個35年,把一“七”分成兩部分。優西比烏做的事和俄利根類似。
【尼】在分享優西比烏的解釋和他的三年半觀點之前,讓我們先看看他是如何解釋《約翰福音》的。因為我們已經討論了一段優西比烏的引文,認為《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一年,那麼,《約翰福音》怎麼可能是三年半呢?
當時優西比烏在寫一本叫《教會史》[74]的書,他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我們對早期教會的很多認識都來自於他。這是一件好事,但也有一個風險。因為優西比烏選擇只分享他認為合理的東西,還有各種各樣他沒告訴人們的事。因為他要麼認為毫不相干,要麼從他的視角認為是異端。比如,那些相信耶穌並且遵行妥拉的猶太人,他們又在哪裡呢?優西比烏沒怎麼講述這一部分,他講述了帕皮亞(早期教父之一),我在《探索耶穌真貌》一書引述過帕皮亞,其實我是在引述優西比烏講述帕皮亞的話。
教父們的很多著作都已毀盡,唯一殘存給我們的,只有來自優西比烏的《教會史》,因此這是一本很重要的瞭解主後三個世紀的書,他(優西比烏論《約翰福音》)是這麼說的:“已經提到的三本福音書[75],在被我們和約翰讀到之後……”,因此,根據優西比烏的資訊來看,約翰讀了馬太、馬可和路加的福音書,這太不可思議了。因為非宗教領域的學術界認為,《路加福音》是寫給一所教會,《馬太福音》是寫給另外一所教會,第三所教會擁有《約翰福音》,讀過《約翰福音》的人不熟悉《路加福音》。而這裡優西比烏所表達的是,“他們說約翰接受他們,見證他們的真實性,但是裡面缺失基督服事初期做的事件。”換句話說,約翰不得不填補祂服事上的空白,即,在前三本福音書裡沒有、只在《約翰福音》有的。
除了耶穌臨受死前的日子之外,其餘事件都發生在前三本福音書的記載之前。他繼續說,“相應地,約翰記錄了施洗約翰坐監之前基督的事蹟,其他三位原福音書作者記載了在那之後的事。”這是優西比烏的觀點,不代表我們的立場,但它表明了優西比烏的觀點是多麼不自然,他把前三本福音書不存在的《約翰福音》事件,插入到他先前承認的一年服事期的前面,“……現在,救贖主的教導和神跡奇事服事的時間,被稱為是三年半,也就是‘一七之半’。”
那麼“一七之半”從何而來呢?(但9: 27)。因此他的老師的老師——當然也是他的老師,把《但以理書》9: 27寓意解經為70年。而他說,不,“一七”是7年,不是70年,“一七之半”是耶穌釘十字架前在地上教導的時間。然後他說,“福音書作者約翰在他的福音書裡將它留心講述清楚了。”優西比烏的意思是,“耶穌的服事是三年半,儘管這是我的寓意解經,但我可以在《約翰福音》找到依據。”
那麼優西比烏在《約翰福音》什麼地方,找到證據來支持三年半的觀點呢?他認同前三本福音書的觀點是一年,《約翰福音》三年半的依據在哪裡?第一次和最後一次逾越節我們是知道的,在《約翰福音》二章和十二章,之前已談到了。《約翰福音》五章未指明的節期顯然被他看作逾越節了,而且他必然也把《約翰福音》六章4節看作逾越節,這就是他說“約翰留心將它講述清楚”的依據,雖然不是直說,但當約五章未指明的節期變成逾越節,就能得到三年多的時間,這就是他的依據。
我們繼續看優西比烏的話[76]。“因此,‘一七’之年就覆蓋了祂在受難前和復活後帶領使徒的整個時期……”,您看到他在說什麼嗎?讓我們先讀完這段話,“因為經上記著說,祂受難前將自己顯現三年半”,在哪裡記載的?《約翰福音》。如果您把約五章未指明的節期當做逾越節,把約6: 4當做又一個逾越節,就得到三年多的時間,這就是他說“經上記著”的意思。
繼續看,“顯現三年半給門徒和非門徒,但是在祂復活之後,祂極有可能與門徒相處了同樣多的時間。顯現給他們40天,與他們同飲食,講述關於神國的福音,正如使徒行傳所告訴我們的。”因此,在優西比烏看來,耶穌在釘十字架前服事了三年半,在復活之後又服事了三年半(觀眾驚訝聲)。有些觀眾說,這是什麼情況?(現場觀眾笑)
【邁】是的,這就是三年半服事時間的由來,也因此得出整個七年服事期的結論。
【尼】因此,三年半理論的起源來自他,依據是來自《約翰福音》,把《約翰福音》五章和六章讀作了逾越節。但他的(七年)服事模式來源於《但以理書》9: 27的“一七”,耶穌在一七的中間被剪除,祂復活後又有三年半時間。新約可沒有提到這個(觀眾笑),如果說40天的確發生很多事情,但三年半?祂這三年半都去幹嘛了呢?
【約】優西比烏從寓意解經的角度先驗性地解讀《約翰福音》文本,他不是看到文本後發現的確有這麼多逾越節,才得出三年半的結論,而是在找尋“三年半”!當他打開《約翰福音》,認定文本裡必然包含三年半,《約翰福音》六章4節,毫無疑問就是它!
【尼】他帶著主觀性去閱讀文本的另一證據是,《約翰福音》五章根本沒有說到逾越節……
【約】他只是看到一個未指明的節期,就說,讓我來把它變成逾越節吧。因為我正在找尋著三年半的時間。
【尼】沒錯,猶太人歷史中有位偉大的拉比叫伊本·埃茲拉[77],他談到閱讀聖經的不同方式。他說,你要瞄準靶心,然後把箭射出去,但是有的人不這樣做,他們先把箭射出去,然後走過去,在箭到的位置畫一個靶心(現場觀眾笑)。我認為優西比烏就是這麼做的,至少在《約翰福音》五章是這麼做的,他對這裡未指明的節期畫了一個靶心。更早期的作者說這個時間範圍太局促了,在四章結尾和五章開始的在兩節經文之間,竟然相隔6個月或1年?果真有那麼長的時間嗎?聽起來不太可能,但他卻那樣解讀了。因為他想獲得《但以理書》9: 27中的七年,並把它當做耶穌服事的模式。
四、手稿文本的查證
目前為止我們都是在談教父,接下來我想給你們分享手稿。手稿的重要性在哪裡呢?在文本研究中,有修訂[78]和變體的差異。修訂,是指我閱讀文本時,認為某處表達有誤,於是進行了更改,這是其一。還有一種叫文本變體[79],文本變體是指:我不僅改變文本,而且我實際上擁有一份原文手稿。
邁克,您舉過《馬太福音》第一章的例子,裡面談到瑪利亞的丈夫約瑟,多年來您和某些人一直在表示,我想也許Lamsa是第一個這麼說的人,他說,丈夫一詞可能具有更高的含義:父親。這一類的解釋在我看來有些牽強,但您其實在表示說,原文是父親,這是一條修訂。當時還是推測,我們還未找到原文文本,後來我找到兩份手稿,都是很晚期的手稿,上面都有“瑪利亞的父親約瑟”。
【邁】那是希伯來文的《馬太福音》。
【尼】是,兩份晚期希伯來文馬太福音,都說到瑪利亞的“父親”約瑟。但如果有人堅持說瑪利亞的“丈夫”約瑟,讓《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互相矛盾,那是各人自己的事兒。
【邁】而且只有13代,不是應該有的14代。
【尼】這就無法真正吻合。但如果您看到文本變體,一切都吻合了。這種情況只是巧合嗎?我不認為是,但是否相信仍取決於您自己。在約6: 4的例子裡,是否擁有原始文本就決定了您要麼是在推測,要麼是從存留下來的數千份手稿裡獲得了某些歷史事件的事實。答案是,我們的確有存留下來的事實。我們要為大家展示九份關鍵手稿,雖然有不止九份手稿,但我們還沒有找全,我們會繼續搜尋。你們可聯繫 John6four@gmail.com。但此刻我們先分享已有的,這些手稿資料來自11至15世紀期間。
1、472號手稿
在分享它們之前,我想先談談所謂“批判版”[80]。是指全球數百位學者梳理了許多個世紀的手稿,他們的工作成果被彙編到一個印刷本聖經,叫尼斯勒和奧倫德(Nestle-Aland/N.A.)版[81]。現在螢幕上的是N.A.第26版,在《約翰福音》六章4節有一個小方格,方格表示被省略或缺失的。“缺失”是一種委婉的表達,意思是“本應該在的”,更加中性的表達是“省略”,什麼被省略了呢?就是整句話,是在472號手稿裡面被省略的。
472是什麼?每一份希臘文新約聖經手稿都被賦予一個葛列格里-奧倫德(Gregory-Aland)編號[82],在這基礎上您能找到更長的手稿名稱,以及它藏於哪個圖書館;然後是pc,它是新約聖經中的校注[83]符號。這裡的每個小符號都有重要含義,它們表示缺失、加添或被更改的內容,或者不同的具有細微差別的詞彙。
而這裡的問題更嚴重一些,在472號手稿裡缺失了整句經文,以及pc,pc不是政治正確[84]的意思,而是表示拉丁語“幾個”的意思。這些編號的意思是,“在472#和其它幾份手稿裡,缺失了約6:4”。哪幾份其它手稿呢?不知道。如何找到呢?不容易。(觀眾笑)。那麼,邁克,您看的是N.A.第26還是27版?
【邁】我的工作基於第26版,該版沒有這句經文。我在拙作的引言裡提到,在472號手稿裡這句經文是缺失的。由於我當時無法獲得它的照片,最終我去了蘭貝斯宮(圖書館)……[85]
【尼】咱們談472號手稿吧,因為它太令人振奮了!
所以根據尼斯勒和奧倫德版(N.A.)新約第26版,472號手稿和其它幾份手稿都缺失該經文。而根據N.A.第27版[86]又是同樣的情況,整節約6: 4在472號手稿是被省略或缺失的。但那是在2004年第八修正印刷版之前。
為了發現這些,我去了許多圖書館,問他們是否有N.A.第27版。他們說有許多啊,我說我需要特定的2004、2005和2006年的,他們說不知道館裡版本是哪一種,他們說都一樣啊,都是N.A.第27版啊!不,其實不一樣,這個是2004第八修正印刷本,而2006年他們把它改成第九修正印刷本時,他們把“整節約6:4在472#手稿是被省略或缺失的”,改成“整節約6:4在1634#手稿是被省略或缺失的”。而1634號是不同的手稿,究竟是哪一個呢?當我做這項研究的時候,我的問題是,在2004和2006的版本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約】對於整本N.A.來說,這個改動是令人困惑的。我和朋友討論這個事兒,打算買一本,因為朋友說,“你沒看到嗎?他們修正了,之前是錯的。”
【尼】因為在N.A.第28版裡根本沒有這個注釋,沒有提到約6: 4的任何事兒。如果您查看N.A.第1至25版和第28版,您不會發現約6: 4有任何問題,您會以為它就在那裡,沒有任何疑問。
【約】我和朋友激烈討論時,他說你為啥不發個郵件問問編輯,找到確定的答案?於是我們就發了郵件。
【尼】我們給N.A.第28版的編輯發了郵件,問他們為什麼2004年版和2006年版不一樣?為什麼這個注釋在2010年版裡,卻不在N.A.第28版?他們回復說,“我們版面空間不夠”。所以我們看看這張圖,所有這些符號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含義。他們說“上面無法容納所有內容,版面空間太小,我們不得去作出取捨,根據既有資料,把我們認為重要的放上去。”在第26和27版,有人認為它是重要的;到第28版,他們說“也不是那麼重要吧,我們把它去掉,人們不必要知道這些。”
那麼,在2004年和2006年之間發生了什麼呢?他們寫了一本書叫《Text and Textwerk》,是用德語寫的……在這本2005年的書裡,您能看到,他們選取《約翰福音》裡的部分經文,對手頭上的所有手稿進行查找,地點在明斯特大學[87],那裡有大量的手稿微縮膠捲合集。
例如,他們選取約6:4,在超過1000份手稿裡查找。結果他們發現,約6:4沒有出現在大量手稿裡。實際上他們給您列出來了,約6:4出現在了162份手稿中,沒有被省略。這162份手稿包含一些非常著名和重要的手稿,如P66和P75手稿。學者們認為這兩份手稿源自第二世紀,如果這個時間是正確的,就比優西比烏還早一些。一位叫Nongbri的學者撰文稱它們是更晚時期的手稿——朋友們,這超出我的專業了。如果我們接受P66和P75手稿的追溯時間,那麼約6:4在第二世紀時就出現在聖經裡了。這意味著,在俄利根閱讀的沒有約6:4的《約翰福音》之外,在羅馬帝國的其它地方,有人讀到了包含約6:4的不同手稿,這是完全可能的。俄利根的獲取途徑也是有局限的。
【約】但他的確有機會獲取許多手稿。我們不可以說俄利根沒看過含有約6:4的手稿,但是如果他看過,他不認為那是重要的。
【尼】他認為那個不可靠。
【約】他本職工作是文本批評家,受過這方面最好的教育。
【尼】換句話說,俄利根在自己的圖書室裡,或許有100份手稿,其中10份含有約6:4,他也許會說,“噢,這是加上去的。”我們也不確定。但我們唯一確定的是我們手上的證據,證明他手上的版本一定是沒有約6:4的。
我們回到《Text and Textwerk》。上面列了很重要的一些手稿,有01,02,03,05,那是梵蒂岡抄本、西奈抄本,這些是重要的新約抄本,共有162份含有約6:4。有意思的是,472號手稿也列入其中。那麼472號手稿到底有沒有約6:4呢,我們很快會揭曉。
在162份手稿後面寫著BYZ,意思是拜占庭,是指“拜占庭文字型別”(Byzantine Majority Text),意思是說,有許多其他含有約6:4的手稿無法一一列出,因生命短暫、版面有限,這本書已經售價五六百美金,如果更厚的話……幸好在Google Books裡我們能找到這一頁。
這僅僅是《約翰福音》,而且是挑選的經文,沒有核查每節經文,就已經售價五六百美金了。那麼,BYZ 1653的意思是說,有1653份手稿裡含有約6:4,但他們只給您列出162份,其餘1491份您儘管相信就好了。現在我就可以告訴您,他們對472號手稿的說法是錯的。我們會說明的,儘管有些複雜,但他們的確錯了。
他們也在這一頁列了其它內容,其中一條是,他們說,列了三份手稿裡面沒有約6:4,其中一份的頁邊空白我們等會兒分析;另外兩份根本就沒有約6:4。
他們為何列出三份手稿呢?因為他們只知道三份。實際上有四份手稿裡都沒有約6:4。他們為何不列出第四份呢?他們把第四份包含在了拜占庭手稿(BYZ)裡。因此他們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目前我在這一頁找到了兩個錯誤,我還沒有核查其他數百份手稿呢。當然,這是約翰的工作。如果我們核查全部1653份手稿,我相信將有不止兩個錯誤。
然後他們說“《約翰福音》六章4節……(德語)“,他們列出第4節裡面帶有“asterisk or obelisk”標記的六份手稿,我們等會再說,好嗎?
我們還看了一份馮·索登[88]寫於1907年的資料,他有一套自己的校注(Critical Apparatus)[89]符號,遠遠早於尼斯勒和奧倫德。他說,“我查遍每一節經文,對照許多的抄本”,他列出兩份省略約6:4的手稿。
朋友們,這個符號非常難懂,光是I 1386我就花了一整天時間來搞明白,這只是一個細節而已。然後是K i20,是省略約6:4的第二份手稿,這是啥意思呢?I 1386指代472號手稿,就是蘭貝斯宮手稿——在蘭貝斯宮手稿裡,該經文被省略了。還有850號手稿,藏於梵蒂岡Barb.希臘504號手稿,我們稍後也會看一下。
我先對“約6:4與472號手稿”做個總結吧。472號手稿藏于蘭貝斯宮,馮·索登說約6:4在其中被省略。我之所以說這個是因為邁克在他的《編年體福音書》裡依照N.A.第26版。《編年體福音書》出版時還很難找到這些資料,來確知472號手稿中究竟有沒有約6:4,除非親自去一趟蘭貝斯宮查考。邁克,您是怎麼做到的?
【邁】我去了蘭貝斯宮,因為當時打算出西班牙語、中文等版本,我想去拍個照片回來。因為我當時知道它不在裡面,因為Nissan告訴我約6:4不在裡面。因此我做了轉錄,把希臘文字放進書中,省略了約6:4,並說明蘭貝斯宮抄本裡沒有這句經文。
所以我想去那裡拍個照片回來。我到了蘭貝斯宮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住所,與他的秘書會見。秘書曾在以色列的基布茲生活過幾年,所以我們相當談得來。但是大主教不在,那天是休戰紀念日[90],是一戰勝利的日子,每個人佩帶罌粟花,店面全關閉了。如果我當時能進去拍下那張照片,我一定會失望至極的,因為472號手稿的確寫有“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我雖費盡周折抵達那裡,卻搞不清楚為什麼,因為這超出了我的專業等級。那是這兩位人士的專業範圍,遠遠超出我的工作等級。我不過是羅列證據,整合進《編年體福音書》,但他們是找到證據的人。
【尼】想解釋一下,朋友們,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不是一件小事兒。要獲得我們需要的資料庫,得花費購置一輛新車的成本,我並沒有誇張,而且還得是一輛不錯的車。
在我們獲得472號手稿前,大致是這麼一個情況。在這裡,馮·索登說,它被省略了。N.A.第26版說,它被省略了。N.A.第27版第8修正版說它被省略了。T&T[91]說,不,就在裡面,且無任何標記。N.A.第27版第9修正版甚至沒提到472號手稿,但提到了1634號手稿,N.A.第28版根本沒提到約6: 4。
2、蘭貝斯宮手稿的特殊符號
那麼,我們就看看真實的蘭貝斯宮手稿吧!蘭貝斯宮位於英國倫敦,它擁有1177號手稿,追溯到11至12世紀,小字體472號手稿表示它用小寫字體,與更早期的大寫字體手稿作對比。您可以看到“逾越節”的字樣,所以約6:4終究是在裡面的。然而,在頁邊空白處有個小東西,一個星形符號,叫obelisk(疑問記號)。在T&T,也就是2005年出版的德語著作《Text and Texwerk》提到,它提到有六份帶有星形和疑問記號的手稿。什麼是星形(Asterisk)或疑問記號(Obelisk)呢?
Asterisk and Obelisk是一部著名的法國漫畫。它是一個雙關語,是指在拉丁文和希臘文手稿中,若存在有疑問的地方,就用星形或疑問記號標注,這些是抄寫符號標記。這部漫畫的創作是關於兩個高盧人和羅馬人打鬥的故事。一個叫Asterisk,一個叫Obelisk,Obelisk是大個子的聰明傢伙。我很小的時候常閱讀《星期日連環畫》,常讀到上面連載的Asterisk and Obelisk,這是它們作為雙關語的意思。這些符號可回溯到亞歷山大港的希臘文文本鑒別。
我們提到過,在俄利根之前,希臘人說,我們把荷馬的著作看作是神聖的,但我們手上的手稿有差異……於是他們把有疑問的地方做上標記。俄利根提到這些,並作如下記述,以下內容選自他的《六文本合參》[92],系統性地比對了《七十士譯本》和《希伯來聖經》:
“……我們用obelus做標記……(obelus是obelisk的希臘文),我們對希伯來文中沒出現的經文標記為obelus;對於我們加添的經文,標記為asterisk,以表示在《七十士譯本》中沒有出現的經文。”因此,當他看到希伯來文有但希臘文沒有的內容,在轉譯為希臘文時,因不確定是否應該寫進希臘文裡,就用asterisk標記。當發現希臘文有而希伯來文沒有的內容,就用obelisk標記,“那些如此期望的人就可接受這些內容,但如果覺得這些內容有所冒犯,就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它們。”
因此,他在告訴您:我認為這些內容不可信,或在某些情況下我不確定其可信度。您自行決定好了。
第四章 畢士大池與真正的救恩泉源
一、編者概述
在古文本研究領域,並非年代越早的手稿越具有權威性。除了《使徒行傳》二十一章25節的例證之外,目前遺存最古老的啟示錄抄本碎片上——獸的數目之考證,再次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儘管尼希米團隊未找到更早期的手稿來支持“《約翰福音》六章4節是添加的”之觀點,但是他們所發現的後期手稿上的疑問記號,和早期教父們對原文手稿的充分論述,均已將真相指示給人們。
以文本考證中的疑問記號為突破口,尼希米又發現在《約翰福音》五章裡,有一節半經文是後來添加的。他非常肯定地相信,耶穌醫治瘸腿38年之人所在的畢士大池,就是西羅亞池。這絕非空穴來風,尼希米從畢士大池和西羅亞池的希伯來文原意、耶路撒冷間歇泉與地形學、拉比們的取水慶典(奠水禮)等,逐一展開講述。
這是本系列講座最跌宕起伏、且收穫頗多的一段希伯來根源之旅。而這樣根源性的解讀聖經,讓我們深深被福音書中耶穌話語的力量所震撼:原來,從猶太人和希伯來文化的角度認識耶穌作為救恩的源頭,竟讓神的話語散發出如此精妙的風采!
二、手稿的年代無關於權威性
1、考古發現的隨機性
【尼】我們已經看到第二世紀的教父,甚至第三、第四世紀的教父,他們讀的《約翰福音》與我們發現的手稿內容一致。因此得知,儘管我們目前已知的唯一遺存版本來自十一世紀,但該內容在第二世紀時已經存在了。而且數百年來,教會內部對此是認可的。比如1643年的沃修斯[93],1777年的皮爾斯[94],1844年的亨利·布朗[95],還有許許多多其他人。所以,幾百年來公認的事實是,教父們閱讀《約翰福音》時沒看到六章4節,更沒有看到“逾越節”的字詞在裡面。
從考古學上講(我在希伯來大學獲得考古學和聖經研究雙學位),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在考古學上的發現是隨機的。您挖掘某個遺址時,只挖其中一部分,開挖該遺址5*5米的範圍,非常大的發掘工作會開挖5到10處這樣的範圍,但是不會開挖整個遺址。因此您的發現是偶然性的。
我們在“死海古卷”上也看到這一點。死海古卷有許多《以賽亞書》的抄本,許多《申命記》的抄本,表明這些書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份《以斯帖記》的抄本,為何呢?因為這種發現是隨機的。如果您發現許多同一樣東西,說明這對他們很重要,但為什麼我們沒有發現一份《以斯帖記》的抄本呢?我們發現的《尼希米記》的抄本大約這麼大,裡面只有幾節經文,非常小。
有句古希伯來諺語,“沒有發現它,不代表事實如此”,所以我們只有已經發現的證據,已知證據來自二、三、四世紀和其它地方,我們沒有一一列出,他們的《約翰福音》裡都沒有六章4節。然後我們發現十一至十五世紀的手稿,以及十六世紀以來學者們的清楚陳述。儘管五到十世紀這一時期的證據很少,但它前後時期的證據我們都有了。
在這裡我想從《塔納赫》裡引個比喻。重點在於,手稿的年代未必決定它的重要程度。換句話說,古老的東西未必是正確的。之前我們看過《伯撒抄本》[96]徒21:25,如果我們沒有西奈抄本和梵蒂岡抄本,會怎樣呢?我們可能會說,《伯撒抄本》是最古老的版本,也許最古老的版本裡《使徒行傳》21:25在告訴我們不要遵行妥拉。所幸的是,我們還有其它抄本,但假如沒有呢?
我們這裡有一份《塔納赫》裡面的手稿,它的名字是“兩種標準”(twofer),這份手稿裡有耶和華的全部母音。它是《耶利米哀歌》三章55節,出自“東方劍橋1753手稿”,是一份很近的手稿了,來自16世紀。然而,在《塔納赫》研究中它被認為是《阿列甫抄本》的直接抄本,《阿列甫抄本》大約完成於西元930年,其中《詩歌智慧書》[97]大幅篇章遺失,所以,學者們想瞭解《阿列甫抄本》中《詩歌智慧書》,就要去查考“東方劍橋1753手稿”。儘管是來自16世紀,仍被認為是《阿列甫抄本》的直接或第二代抄本,因此被認為具有《阿列甫抄本》一樣的高度可靠性。
在這裡我們看到耶利米哀歌三章55節說,“耶和華啊,我求告你的名”。耶和華帶有全部的母音,太棒了,大家阿們嗎?
【觀眾】阿們!
【尼】重要性在於,晚期的手稿不代表它價值更低,它可能是我們手上沒有的更早期手稿的複抄本。當然,我們有“東方劍橋1753手稿”的更早期手稿,只不過沒有完整的《詩歌智慧書》。再請約翰分享一個我很喜歡的例子,是約翰和我分享過的新約手稿裡的。
2、《啟示錄》獸的數目之例證
【約】你們可能聽過這個事情,早在2005年,這張特殊的紙莎草手稿的年代被界定時,它成了《啟示錄》的最早手稿碎片,上面的經文提到獸的數目。
【尼】稍等,我打斷一下,您要說的內容將毀滅許多書籍和圖書館,可否口下留情?我們需要那些末世教導,不要這麼殘忍。
【約】這條特殊的經文說獸的數目是616。
【尼】大家可以看到是用希臘文寫的,600,10和6,
【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對啟示錄評注的基督教書籍將被統統燒毀了,這將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篝火(觀眾笑),《編年體福音書》也將前途未卜……(討論小組笑)。由於這是最早期的,如果您認為越早期的手稿越準確的話,它就會帶來一定的結果,但有時候最早期的手稿不是最準確的。我們手上也沒有最早期的手稿。我們談論過的教父愛任紐,我讀一下他是怎麼論述這個話題的。請記得,愛任紐是坡旅甲的門徒,坡旅甲是約翰的門徒,所以他認識那認識約翰的人,他說,“在最被認可的最古老抄本裡發現的數字,寫作者和約翰曾經面對面見過,寫作者作見證說……數字是666,我不知道怎麼會有人犯這個錯誤……改變了中間的數值,從中減去50,因此把60年替換為……”
【尼】“因此把60年替換為10年。”換句話說,在愛任紐的時代,在“紙莎草紙115手稿”[98]之前大約100年(“紙莎草紙115手稿”被發現於埃及),我們看到愛任紐論述說,“我們瞭解616,但《約翰福音》最可信賴的抄本,雖然我們手上沒有它,上面是666。”他說,不僅是因為最可信賴的抄本,還因為那些認識約翰本人的人們。我們問他們,他們告訴我們說“616是個錯誤,應該是666”。那麼重點來了,我們手上有遺存的最古老啟示錄抄本,告訴我們是616;而愛任紐說,“不對,已經不再存在的古抄本,和見過約翰本人的人們都說是666”。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儘管您手上有一份古抄本,不能說明它一定是保存下來的最完美版本,還必須對比所有的證據。愛任紐的清楚陳述使我們得知,666是正確數字,而非616。所以我們最後得到獸的數字,不得不依據教父們的說法。如同《約翰福音》六章4節的情形,我們有後期手稿支持約6:4是添加的觀點,即便我們沒有早期手稿來支持這一觀點,但我們有教父的支持,正如《啟示錄》裡獸的數字這個例子(觀眾掌聲)(觀眾歡呼)。
3、我們能否信任目前的聖經文本?
進入下一個話題前我先說個問題,也許是現場觀眾的疑問。可能有人會說,既然616和666以及約6:4,被標記為不可靠的、不忠實于原文的,我們該怎麼做?要扔掉我們的聖經嗎?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因為這項工作已經持續數個世紀,人們在不斷地詳查和鑒別,努力確定原稿的用詞。我們查考古文獻資料、教父作品和聖經手稿,人們在整理、核查、尋找和比對,你們現在擁有的希臘文新約聖經——其實不單是希臘文,他們還查考古敘利亞語和拉丁語,現在又在查考希伯來語和其他資料——我們所見證的是一個詳查的過程,以證實該版本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可信賴的文本。
【邁】阿們!阿們!(觀眾掌聲)
【約】其實,文本變體[99]的問題是令人不安的,這可是神的話語啊。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關於神的話語究竟是什麼,我們遇到的是多選題。其實,我們不應該因此感到困擾,因為這些都是對原始文本的見證。我們沒有原始文本,但這些是對它們的見證。
如果外面發生一起交通事故,而且只有一個人看到了,就不存在不同的描述,只有一種描述,不論描述的對錯,都不會有變數(variance)。如果有兩個人看到了,他們的描述在細節上可能略有不同,這時就存在見證方面的變數(variance)。
我們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文本變體(variants),因為我們擁有5800份希臘文手稿,來為原文做見證。我們聖經中的文本變體如此之多,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見證資料。由於擁有對原始文本如此多的見證資料,我們對聖經記載的事件就非常確定,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事件的發生,比耶穌的受死、埋葬和復活更令我們感到確信!絕大多數情況下,也不存在改變主要教義的文本變體。
我見到聖經中最嚴重的文本變體,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使徒行傳21:25的變化。如果您不是泛泛讀經的話,您一定能識破那一句經文的變化,因為整本聖經其餘的經文,足以讓您明白原文的本意。
【邁】是的!(觀眾掌聲)正如我們在《證據模式:摩西的爭議》[100]所看到的,儘管有各種懷疑,提出各種論點,但是沒有一份手稿說妥拉不是摩西寫的。幾千份遍及全世界的、甚至寫於中國的手稿……它們都在講述同一件事情。
【尼】是的,有七卷中國的猶太人保留下來的妥拉,我考查了其中兩份。它們和全世界其它妥拉的說法都一樣。
【約】當我們在聖經博物館[101]時,我們發現四字聖名(Tetragrammaton)帶有全部母音,就在被展出的那個名字上。
【尼】是的,來自中國的聖經不是妥拉書卷形式,而是一本書。有四處地方有耶和華的全部母音,就在聖經博物館的中國聖經裡,對全世界開放。
我對《塔納赫》的研究是這樣的:儘管有數千份手稿裡沒有全部的母音,但是現在我們有1776份有全部的母音。我在比對它們的差異,努力找出原文是什麼,這就是我在做的研究。我在尋求真理,當我坐下來做這項課題時,我對約翰說,“我不是要來證明邁克是對的,我只想知道他是對是錯,如果他錯了,我會去告訴他說,邁克,這裡錯了”。
我的研究結果表明他的觀點是有證據支持的,而在座的各位信徒得自己做決定。我總是勸大家,在宇宙創造主面前,每個人都要戰兢敬畏地禱告和親自查考,阿們?(觀眾掌聲)
三、《約翰福音》5:3-4勘誤
【邁】阿們!尼希米的背景不僅有聖經手稿研究,還有考古學,那麼,《約翰福音》裡還有一處值得注意的地方。
【尼】這是又一處文本變體,在《約翰福音》中被我們發現了,五章第1節,“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這是未命名的節期,我們今天已講了很多,“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102],旁邊有五個廊子;”
今天的多數學者和考古學家,把畢士大鑒定為古城西邊的一處地方,在今天穆斯林區的聖亞納教堂[103]。之前那裡是一個古老的水池,他們說那就是畢士大教會(The Church of Bethesda)。畢士大(Bethesda)可能是希伯來文或亞蘭文,類似於Beth Hesda,意為“公義之殿”。儘管希臘文裡出現了文本變體,為Beth Zeta,意思是“橄欖樹之殿”。所以,那個池子的具體位置是不明確的,但是,如果您閱讀新約文本,會很清楚這就是西羅亞水池。
1、畢士達池實乃西羅亞池
西羅亞池是耶路撒冷的一處池子,池水源自耶路撒冷主泉:基訓泉[104]。流經希西家隧道,是希西家王在亞述帝國入侵時挖掘的S型隧道,然後水被分流到西羅亞池裡。用希伯來語說是“示羅亞赫(Shiloach)池”,Shiloach意思是“被送來的”,它被稱作Berekhath ha-Shiloach“被送來的池子”,因為水從基訓泉而出,流經隧道,送入城區,有備無患,以保護好水源。
為什麼我說那裡是西羅亞池呢?我們來讀《約翰福音》五章3節,“裡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下一部分內容,我把它放進括弧裡,在英王欽定版是不在括弧裡的。下一部分內容在許許多多抄本裡都沒有,(“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先下去,無論害甚麼病就痊癒了。”)當您讀這節經文時,它提到的內容在新約其它地方是找不到的,《塔納赫》裡更是沒有。我很欣賞約翰對這一點的解說。
【約】如果這節經文是準確的,它所教導的資訊對整本聖經來說都是陌生的,表示說只要跑的快,把其他人推倒,然後下到水中,就可以得到救恩了。
【尼】對,我想到喬治·科斯坦紮[105]在火中的模樣,他推倒一位老太太,說“別擋道”。因為誰先下去,就得救啊!(邁克和觀眾笑)我認為許多手稿都沒有該內容的另一原因是,它描述了某種非常異教的東西,有天使下來攪動水池,就能醫治人?(觀眾小聲說話)這是個奇怪的概念。如果您閱讀大多數的譯文,比如NRSV[106]裡面就沒有《約翰福音》五章4節,第3節後半部分也不在裡面。在NIV(新國際譯本)裡也沒有。
有意思的是,我們看到手稿後發現了什麼呢?我們發現了好朋友——Obelisk(疑問記號),《約翰福音》五章3B(3節的後半句)以及4節,在俄羅斯聖彼德堡國家圖書館的“Majuscule 41”手稿,以及九世紀的“Greek 34”手稿,在頁邊空白處均有疑問記號,表示作者不信任這句經文,認為它不應該出現在那裡。您看到這裡都是疑問記號,包括3節後半句和整個4節經文。約翰發現了許多這樣的手稿,我只分享兩份,因為我們時間不夠了。
“Miniscule 348”是更晚期的手稿,來自1022年,和我們查考的其它大量手稿年代差不多,它來自米蘭的盎博羅削圖書館[107]。《約翰福音》五章4節也在頁邊空白處標記了疑問符號,您可以看到,在上方右側。這些疑問記號都在說,這句是值得懷疑的經文。為何值得懷疑呢?因為有些抄本裡根本沒有它,不是嗎?我給大家看的抄本裡的疑問記號,讓您知道不僅約6:4存在疑問記號,因為中世紀的抄經人看到某些經文後認為,它們不應該出現在那裡,於是以存疑記號注釋那節經文。
我們繼續,約翰福音五章6到8節,“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所以這裡不關天使的事兒,而是說水被攪動。
根據這個說法,我馬上想到耶路撒冷的水體類型,它只可能是西羅亞池或“被送來的池子”。我為何這樣說呢?我們繼續往下看,“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觀眾笑)現在我們要看看為什麼……
在講解安息日拿褥子的事之前,我們先談談西羅亞池。西羅亞池或“被送來的池子”位於耶路撒冷,注入的水來自基訓泉。基訓泉是一種特殊的泉水,被稱作間歇泉,在一個週期內從蓄水層噴出泉水。
我們先聊聊什麼是溫泉吧。井是人們挖到蓄水層而建造的,溫泉是地面裂縫因受壓,而從蓄水層地下湖裡噴發出的水。以色列是一塊依賴天然溫泉的土地,儘管有一些井,但主要是溫泉,尤其在山地。如果沒有溫泉,就無法定居。您去到任何一處古城,某個地方總會有溫泉,泉水從蓄水層湧出來。間歇性溫泉是週期性湧出來的。之所以這樣,他們認為是有某種地下洞穴,洞穴的水漫到一定高度時,水就向外溢出,通過間歇泉湧出來。
它是耶路撒冷外非常好的一處溫泉,我很喜歡,因為我妹妹住在那兒,我去過許多次。那地方叫伊馬布阿(Ein Mabua),意為“冒泡的泉水”。您去到那裡,站在水中,開始是完全幹的,是一座空池子。您看到底部稍有潮濕,但水位甚至不及腳踝。站立40分鐘,水就出來了,它的週期是40分鐘。水位上來後,停留一陣子,然後慢慢退去。上來,再退去。當水位上來時,速度很快,不到5分鐘,水就滿了,意想不到的快。如果你在裡面睡著,可就麻煩了。所以,它被稱作間歇泉,也叫虹吸泉,因為所發生的是虹吸現象。
以色列有四處間歇泉(全球大約100處),這四處其中一個在以色列北部,叫Ein el Jinn。是阿拉伯名字,意思是Jinn的溫泉,就像genie(精靈)這個詞一樣。所以是“鬼怪或天使的溫泉”,是不是耳熟?(觀眾歡呼)所以,圍繞這些溫泉存在各樣的迷信。因為他們不知道為何每40分鐘水就湧出來。對於基訓泉來說,一天湧出三次,人們不懂水為何突然湧出來,其它時間水是慢慢湧出來。所以當時的百姓信奉的是,泉水裡住著一個精靈,它會攪動水往上來,那麼,這個迷信是怎麼出現在《約翰福音》呢?
人們一代代抄寫這樣的經文,可能有一位來自耶路撒冷的抄經人,說:“噢,我知道水為何被攪動,因為有天使來攪動它們啊。”他很可能一開始把這話寫在頁邊空白處,下一個抄經人就把它放進正文了,事情就是這麼發生的。所幸有一些抄經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用疑問符號作了標記,因為他們抄寫的原件沒有這些經文,就像《約翰福音》六章4節一樣。所以這一節半經文是由迷信之人加上去的。但是,在我看來這毫無疑問是在談基訓泉,它灌入西羅亞池。
那個在五個廊前瘸腿的人,躺在褥子上,根據地形學,他是躺在西羅亞池的前面,同時也是依據經文所說,不是根據3節和4節(因為它是添加的),而是根據7節的準確說法,他說“水動的時候”。因耶路撒冷間歇泉的週期是一天三次——我不是第一個發現的人,在二十世紀之前,每個人都相信這是瘸腿者被醫治的地點。如果您詢問兩百年前任何在耶路撒冷的人,他們會指示您基訓泉的位置。只是後來到1905年,他們把它指向了聖亞納教堂。
現在,在談到重點前我想再說一分鐘,這個太重要了,您知道嗎,我的朋友基斯稱之為“點球成金”[108]。在整個故事中,中心資訊都是圍繞地形學的。有人把以色列的地形學稱作第五本福音書。當您明白以色列地形學,這些東西就躍然紙上了。耶路撒冷的地形學是理解《約翰福音》五章的關鍵。
2、耶穌刻意違反《米書拿》安息日規定
在談論它之前,我想先說說,為什麼那個人拿起褥子走開是備受爭議的,爭議點是什麼?這和猶太教法利賽人對做工的定義有關。拉比對做工的定義是非常技術性的,我稱之為默守陳規。諷刺性的是,只有一件事不屬於安息日做工,就是生孩子。我可不是開玩笑。其中禁止做的一件事是,在安息日把東西從家裡攜帶出去。具體說是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109],沒有時間細說這個了。但在安息日攜帶東西是被禁止的。
我先父是位拉比,每當他離開家時,口袋裡連一把鑰匙都不放,因為那被認為是做工。然而他們卻告訴我,你可以背上扛個沙發,整天在自家樓梯上上下下,只要你不帶著沙發(甚至鑰匙)離開家。實際上,根據正統猶太人和古代法利賽人規定,在安息日甚至不可以在西服翻領或口袋放手帕。所以,《約翰福音》的那個人被耶穌醫治後站起來,拿起褥子走開,違反了法利賽人的安息日規定。
拉比在《米書拿》“節期供物篇”一章8節說,“安息日律法如同重山懸於青絲,經文乏善可陳,律法多如牛毛。”他們意思是說,在出埃及記31:13有一個字,“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務”這個字可以翻譯為“當然”,但是拉比把‘務’字解釋為數千條律法。他們說,由於上下文是建造帳幕,所以有關建造帳幕的一切事,都被定義為安息日的做工。他們建造帳幕時,必須縫紉,那麼縫紉就是被禁止的(我不會縫紉,但是會的人這麼告訴我)。要縫紉,就要撕扯,拉比在安息日禁止的一種勞動形式就是撕扯。我在這裡不是開玩笑,但你真的不可以在安息日撕廁紙。在以色列人們去超市購買符合猶太教規的廁紙,是在安息日之前提前撕好的。根據拉比規定,這是實實在在違反安息日條規的,這樣做的懲罰是死。所以您現在明白耶穌反對的是什麼了吧?以及那個被醫治的人所反對的,當他拿起褥子走開,觸犯了法利賽人的安息日規定,懲罰就是死。
3、住棚節奠水禮的真相
現在來看看,為什麼這件事發生在西羅亞池很重要呢?答案必然與耶路撒冷每年的中心慶典有關。中心慶典從西羅亞池開始,它是最重要、最大規模的——我不該說最重要,我認為它不重要。但是一世紀的拉比認為它是最重要的。它無疑是最大規模的年度慶典,被稱作Simchat Beit HaShoevah,字面意思是“在取水的殿中歡喜快樂”,是住棚節期間慶祝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該慶典的目的,是從西羅亞池取水。他們會從西羅亞池取出基訓泉的水,然後在這場大型慶典和儀式裡把水帶到聖殿。大祭司手拿水壺,把從西羅亞池取來的水倒向祭壇。那麼妥拉什麼地方要求我們舉行奠水禮呢?這裡談的就是奠水禮,有人知道嗎?
【觀眾】《約翰福音》七章。
【尼】《約翰福音》七章是妥拉嗎?(邁克和觀眾笑)
妥拉哪裡要求我們取基訓泉的水並澆奠到祭壇呢?妥拉對此沒有任何要求。《米書拿》對這個儀式有所描述,我給大家讀一下。這裡很重要,“奠水禮是如何舉行的呢?大祭司從西羅亞池取水,用三隻木筒[110]灌入一隻金色的水壺,在八天期間他將澆出一木筒的水作為奠水。”八天指七天住棚節節期和第八天,有時人們把第八天稱為最大之日。他們不是八天都舉行取水儀式,但是八天期間都舉行澆水儀式,“他們對澆水的人說,‘抬起手來’,因為之前有位祭司把水澆到自己腳上了。”
很奇妙的是 《米書拿》和約瑟夫[111]的書中,都記載了把水澆到腳上的事件。約瑟夫給出了他把水澆到腳上的緣由——但如果是一位法利賽人閱讀《米書拿》,他早已知道原因是什麼。大祭司通常是撒都該人,撒都該人只相信“書面妥拉”[112],不相信“口頭妥拉”。奠水禮是地地道道的“口頭妥拉”,它沒有“妥拉”的依據。拉比們討論奠水禮的起源,為此舉行了一場辯論會。一位拉比說它源自摩西在西奈山的一條律法,屬於某種特殊類別的口頭律法,所以在書面妥拉裡沒有任何依據。其他拉比說,不,這要追溯到創世六日時。這是一種很深奧的說法,當拉比們說,追溯到創世六日,其真正意思是,承認這項儀式早於摩西時代,如果它早於摩西時代的話,這就讓我感到擔心了,它實際來自哪裡呢?
我簡單說說奠水禮吧。當他們從西羅亞池取水時,拉比們在水壺前面跳舞,耍著火把,而火是中心資訊,是中心部分。記載說,火光充滿耶路撒冷城,沒有一處院子不被照亮。所以在這個水的前面,耍著火把跳著舞,描述的是這些大拉比們把火把扔到半空,然後朝聖殿方向平伏在地,再跳起來抓住火把。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花招,他們用火伴舞,用音樂伴舞,以此把水帶上去。那麼這水的功用是什麼呢?奠水禮的作用是什麼呢?
拉比給了兩種不同解釋。第一,把水澆到祭壇上——請記得,以色列的住棚節開始在雨季前,住棚節之後,過幾個禮拜就是雨季了。有時要過一個月甚至更久的時間,因年份而異。但住棚節是在雨季之前。拉比解釋把水澆到祭壇的目的(妥拉沒有這麼要求),是讓雨水在下一年降到以色列。還記得拉比們以音樂和雜耍火把來伴舞嗎,那是祈雨舞(rain dance)(觀眾笑)所以它的確是早於妥拉[113],有人會感到驚訝!
【尼】對取水儀式和跳舞的另一種解釋,根據猶太教文獻,是讓聖靈降在以色列。所以他們說,不只實際雨水的形式,還有聖靈的澆灌。他們把這和妥拉的一節經文聯繫起來,是以賽亞書的一節經文。順便一說,《米書拿》的一條表述是:任何人如果沒有見過取水慶典儀式,沒有見過通往聖殿山的祈雨舞,那他這一生就沒見到過真正的慶典。這被稱作最終事件(ultimate event),最終的舞蹈和儀式。目的是把慶典帶入耶路撒冷、把水帶上聖殿山,讓聖靈澆灌、讓雨水澆灌以色列。
那麼,這在宗教研究裡面被叫做交感巫術,什麼是交感巫術?我想傷害某個人,就用針刺他們的布娃娃,我想讓雨水落在以色列,就從有魔鬼或天使居住的溫泉取來水,用水壺澆灌下去。這是人們的想法,這不是妥拉的規定。所以那位大祭司才把水澆到自己腳上,他說,我不願遵從這項儀式,這是法利賽人要求做的。因此他把水澆到自己腳上,而沒有用錯誤的獻祭去污穢祭壇。
那麼,拉比規定這個奠水禮的依據是什麼?他們引用《以賽亞書》十二章2-4節經文,這其實是安息日結束儀式的祈禱文(希伯來語)。它說,“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拉比說,當我們下去用歡慶的儀式,舞蹈和音樂從西羅亞池取水,我們就是從“被送來的池子”取水,就是從救恩的泉源取水了。然後經文繼續說,“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將他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提說他的名已被尊崇。”拉比說,我們可以這麼做。他們就去西羅亞池,去祈求聖靈。他們沒說“祈求”這個詞,但本意如此:我們去從一天噴湧三次的溫泉那裡取水,好讓聖靈降臨在以色列。這是他們所相信的。
這是理解耶穌醫治瘸腿者的上下文關鍵。那個人說,我無法被醫治,無法得拯救,因為不能下到被攪動的水裡。耶穌說,你想行走嗎,想得到醫治嗎?你不需要那個魔法水,你不需要那個所謂救恩溫泉的水,它不過是一個流水的池子。如果你想得到救恩(Yeshua)[114],你就能得到,而不是來自一個池子。你可以從別的方式得到救恩,這就是《約翰福音》五章在說的內容。
這條內容的證據,是《約翰福音》七章37節,我想請邁克宣讀出來。在住棚節的末日,七日慶典後,在以跳舞的方式取上來西羅亞池的水以後,到最後一日第八日祭司正在澆水的時候,耶穌站在聖殿,祂做了什麼呢?
四、耶穌才是救恩的泉源!
【邁】“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觀眾鼓掌、歡呼)
【尼】這就是《約翰福音》七章37節。在住棚節的末日,在七天跳舞過後,第八天的澆水之時,奠水禮(Simchat Beit HaShoevah)慶典的末日,耶穌說,你們想讓水澆下來嗎?你們想讓聖靈澆灌下來嗎?這可不是來自一壺溫泉池子的水。救恩會臨到你們,如以賽亞的美好預言一樣,卻是以不同的方式臨到。我認為祂在《約翰福音》五章對那個人講的話,意思是說,“你想得醫治嗎?拿起褥子行走吧。”你不需要流動的水分子的救恩。救恩之水來自不同的地方,來自彌賽亞。我認為這是《約翰福音》五章最真實的上下文資訊。
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您閱讀現代基督教對這一章的研究,他們設計了整個故事,把它解說成,人們在敬拜希臘神阿斯克勒庇俄斯[115]——阿斯克勒庇俄斯是一個異教之神,人們到牠的廟裡,打個盹,他們會睡在廟裡面,認為睡一覺就被醫治了。現代基督教學者的解說是,“噢!《約翰福音》五章是(耶穌)對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回應,以顯明基督比阿斯克勒庇俄斯更有能力。”錯了!在一世紀的猶太語境裡,這不過是耶穌對取水儀式的回應。猶太人認為取水儀式能讓他們獲得救恩,只要他們自己灌滿水壺,再(違背妥拉)把它澆到祭壇上就可以了。祂說,不是這麼回事兒,你們獲得救恩的方式只能是神差遣[116]的彌賽亞(觀眾鼓掌歡呼)。我作為一個迦來特派猶太人,給你們講說它上下文的意思:約翰福音的資訊是,那個溫泉和水池不是被差遣來的——記得那個溫泉水池被稱作西羅亞池“送來的”,而祂——彌賽亞才是被差遣來的,祂能賜給你們救恩(觀眾歡呼)(號角聲起)嗚!!!
【邁】二十年前,尼希米說,“許多人找到我,問我為何不信耶穌”。我對尼希米說,“如果你現在成為信耶穌的人,會把一切攪亂的。”(尼希米和觀眾大笑)
因為您在把耶穌真實說的話和祂的教導,講給那些不聽從耶穌的基督徒。您這麼做是因為相信祂說的話是對的,他們說信耶穌卻不這麼去做,這真是絕妙極了!一個基督教之外的人在告訴基督徒耶穌說的話。您讀了希伯來文馬太福音,讀了希臘文,還告訴我們考古學的背景,這真是絕妙極了!
[1] 譯注:安息日晚間直播(Shabbat Night Live),是邁克·儒德的事工A Rood Awakening(儒德的喚醒)系列節目之一,每週五晚在YouTube英文頻道準時開播。
[2]譯注:希臘語新約(Novum Statementum Graece),是新約聖經的重要版本。原文為古希臘語,是大多數現代聖經翻譯及考證的基礎。因其最具影響力的編輯尼斯勒(Eberhard Nestle)和奧倫德(Kurt Aland)而被稱為尼斯勒-奧倫德版聖經(Nestle-Aland)。
[3]譯注:這裡為約翰·拉爾凱的口誤,根據上下文,所指應該是妥拉,而非十誡。
[4]譯注:聖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又譯“約翰一世”,是一位重要的早期教會神父,曾擔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其出色的演講、雄辯能力,譴責當政者與教會內部濫用職權、進行嚴格苦行而聞名。
[5]譯注:耶路撒冷會議(The Jerusalem Council),又稱使徒會議,或是耶路撒冷大會,大約是西元49年在耶路撒冷召開。在古代大公會議舉行之前的各種會議中,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它被天主教會與東正教會視為後來大公會議的原型與先趨,而且是基督教倫理的關鍵部分。(維琪百科)
[6]譯注:公認文本(Textus Receptus),歐洲宗教改革時期出版的希臘語新約文本,由天主教學者伊拉斯謨所編訂,為印刷文本,而非手抄本。公認文本是宗教改革時期眾多譯本所依據的文本,著名的英王欽定版聖經(KJV),就是根據此文本翻譯的。
[7]譯注:塔納赫(Tanakh),也譯為“希伯來聖經”,指舊約聖經部分。
[8]譯注:《伯撒抄本》(Codex Bezae),是一部新約聖經手抄本,可追溯至西元5世紀;其中包含了大部分希臘文和拉丁文版本的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以及約翰三書中一小部分。《伯撒抄本》是西方文本類型(Western text-type)的代表性抄本。
[9]譯注:《聖耶福列木再撰抄本》(Codex Ephraemi Rescriptus),是一部五世紀的希臘聖經手稿,有時被稱為四大聖典之一;目前手稿並不完整。
[10] 譯注:翻版複寫(palimpsest),即重新書寫羊皮書卷或書卷,把全部或部分原有的文字內容刮去,在上面另行書寫新的內容。
[11] 譯注: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又譯為“西乃山抄本”或“西乃抄本”,是一系列以通用希臘語寫作的《聖經》抄本;于4世紀以安色爾字體寫成,包含《新約聖經》及《舊約聖經》;是現在年代最早的《新約聖經》抄本,在新約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
[12] 譯注:《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最重要的希臘語聖經手抄本之一;此抄本於西元4世紀完成,以希臘語安色爾字體抄寫而成,品質極高。
[13]《亞歷山大古抄本》(Codex Alexandrinus),是一部5世紀希臘文聖經的手稿,包含了希臘舊約和希臘新約的大部分內容;與《西奈抄本》和《梵蒂岡抄本》一起,它是聖經最早、最完整的手稿之一。
[14] 譯注:P74手稿(Papyrus 74),是一份希臘文新約抄本,含《使徒行傳》和《大公書信》(Catholic Epistles)等內容。研究認為,該手稿是西元七世紀的作品。
[15] 紙莎草紙(Papyrus),是一種類似於厚紙的材料,古代用作書寫表面。
[16] 譯注:布魯斯·曼甯·梅茨格(Bruce Manning Metzger)(1914-2007),美國聖經學者, 聖經翻譯和文字評論家,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新約學者之一。
[17] 譯注:《希臘文新約文本指南》(Textual Guide to Greek New Testament),是基於廣為人知的《希臘文新約文本評注》一書,專門為那些沒有受過正規文本鑒別訓練的翻譯人員而設計編輯的一本書。
[18]蓋烏斯·尤利烏斯·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西元前100年——西元前44年,史稱凱撒大帝,傑出的軍事統帥、政治家,以其優越的才能成為羅馬帝國的奠基者。
[19] 拜占庭文本(Byzantine Majority Text),希臘新約遺存手稿中數量最多的形式。
[20]譯注:前三本福音書均記載耶穌登山變相時,彼得對耶穌說要搭三座棚子,即指預備接下來的住棚節。
[21]譯注:詮釋範疇(Explanatory Scope),指一種理論可解釋的內容之多少。如果一種理論能解釋更多的東西,那麼它的詮釋範疇就更大。
[22]譯注: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又稱優西比烏斯、遊社博、歐瑟伯,是巴勒斯坦地區凱撒利亞的教會監督或主教。由於他對早期基督教歷史、教義、護教等貢獻,被一部分人認為是基督教史之父。
[23]譯注:《教會史》(Church History),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教會史,在史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該書試圖重現從使徒時代到西元324年這三個世紀的教會歷史。全書共十卷,第一卷記載耶穌基督的生平,第二至第七卷敘述從基督教產生一直到羅馬皇帝戴克裡先上臺的時期,第八卷記述戴克裡先統治時期對基督教的大逼迫,第九卷記載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西方的勝利和馬克西敏在東方的再次逼迫,最後一卷記述了教會獲得寬容、和平以及羅馬帝國支持的歷史過程。優西比烏的《教會史》是瞭解早期教會和羅馬帝國不可或缺的經典著作。該書不僅為早期的教會史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而且為教會史的寫作立下了一種典範。這部著作使優西比烏躋身於約瑟夫、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偉大的歷史學家之列。(選摘自《教會史》,瞿旭彤譯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4] 譯注:紮卡裡·皮爾斯(Zachary Pearce),1690-1774,有時被稱作撒加利亞,是一名北愛爾蘭班格爾和英國羅切斯特市的主教。
[25] 譯注:格哈德·約翰·沃修斯(Gerhard Johan Vossius),(1577年,海德堡 – 1649年,阿姆斯特丹),荷蘭語古典學者和神學家。
[26] 譯注:尼希米所贈之書是拉丁文寫成,其觀點與邁克·儒德花費幾十年研究而得出來的思想不謀而合。
[27] 譯注:亨利·布朗(Henry Browne),1804-1875,英國古典和聖經學者,致力於翻譯經典著作和闡明聖經事件年表。
[28] 譯注:阿提卡(Attica),古希臘的一個地名,位於首都雅典周圍,以阿提卡半島為核心輻射周邊地區。
[29] 譯注:使徒教父 (Apostolic Fathers),指基督教使徒以後的初代至二代的教會作家,是生活於一世紀後半至二世紀中葉前的基督教人物。他們之所以被稱為使徒教父,是因為他們曾直接接觸過,或受教於,耶穌的使徒,或是使徒的門徒。使徒教父這一名稱始自十七世紀,起初有五位,後來另加了三位,共八位。(維琪百科)
[30] 譯注:布魯斯·曼甯·梅茨格(Bruce Manning Metzger)(1914-2007),美國聖經學者, 聖經翻譯和文字評論家,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新約學者之一。
[31] 譯注:巴特·丹唐·埃爾曼 (Bart D. Ehrman,1955-),美國新約學者,專注于新約文字評論和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和發展。他撰寫和編輯了30本書,其中包括三本大學教科書。他還寫了六本《紐約時報》暢銷書。
[32] 譯注:《新約文本》(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自1964年首版就成為基督教歷史與聖經研究的課程標準文本,這本書有望成為新一代學生使用的最權威資源書。
[33] 譯注:《托塞夫塔》(Tosefta),猶太巴比倫亞拉姆語,意為“補充”,是2世紀後期米書拿時期的猶太口頭律法彙編。在許多方面,Tosefta 是對《米書拿》(Mishnah)的補充。
[34] 譯注:《塔納赫》(Tanakh),是猶太教正統版本的《希伯來聖經》,是猶太教的第一部重要經籍,基督教稱之為“希伯來聖經”或“舊約聖經”。
[35] 譯注: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基督教神學家,基督教早期教父,亞歷山大學派的代表人物。為了跟同名的教宗克肋孟一世(他被稱為羅馬的革利免,Clemens Romanus)區分,而常被稱為亞歷山大城的聖革利免。
[36] 譯注:亞歷山大教導學院,又譯為教理學院、聖道學校,於190年前後,由潘代諾創建於埃及亞歷山大,以哲學問答的方式來教導基督教神學。它是亞曆山太學派的中心,對於基督教神學有很大的影響力。 許多重要的基督教早期教父,如革利免、俄利根等人,都出身於此。(維琪百科)
[37] 譯注: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按其奠基者亞歷山大大帝命名。先是作為馬其頓帝國的埃及省總督所在地,後來成為埃及王國的首都,隨後,很快成為古希臘文化中最大的城市。在西方古代史中其規模和財富僅次於羅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猶太人城市,七十士譯本在那裡完成,也是早期基督教的主要中心。
[38] 譯注:俄利根(Origen),又譯奧利金,約185年一254年,生於亞歷山大港,是古代東方教會最為著名的教父,亞歷山大學派的主要代表,基督教著名的神學家和哲學家。
[39] 譯注:《雜記》(Stromata or Miscellanies)是革利免對基督宗教與神學信仰的隨手記錄。
[40] 譯注:“恩年”一詞在和合本被翻譯為“禧年”。根據英文the acceptable year, year是單數,翻譯為“恩年”是更正確的表達。
[41] 譯注:這句更確切的翻譯是“報告耶和華悅納人的恩年”(proclaim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42] 譯注:愛任紐(Irenaeus),生於西元2世紀小亞細亞的早期基督教主教。傳統認為,他是使徒約翰的門徒坡旅甲(Polycarpus,69-156)的學生。最重要的著作為《反異端》(Against Heresies),駁斥了當時日漸茁壯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s)。其著作奠定了早期基督教神學發展。
[43] 譯注:聖坡旅甲(聖公會譯聖波利卡,Polycarpus,約69年-155年)西元2世紀時士每拿(今土耳其境內伊茲密爾)主教,是教會史上首先詳細記錄的殉道者,86歲時殉道。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都尊其為聖人。史載坡旅甲是“約翰”的門徒。(參考維琪百科)
[44] 譯注:諾斯底主義的“諾斯底”一詞在希臘語中意為“知識”,諾斯底是指在不同宗教運動及團體中的同一信念,這信念可能源自於史前時代,但卻於西元的首數個世紀活躍于地中海周圍與伸延至中亞地區。這信念的主旨就是透過“靈知”來獲得知識。“靈知”在希臘語原文,是指透過個人經驗所獲得的一種知識或意識。(維琪百科)
[45]譯注:瓦倫丁主義(Valentinianism),是主要的諾斯替教派基督教運動之一。它由瓦倫丁努斯(Valentinus)在西元2世紀創立,其影響力廣泛傳播,不僅在羅馬,而且從西北非洲到埃及,再到東部的小亞細亞和敘利亞。在運動歷史的後期,它分裂成一所東方學校和一所西方學校。 維琪百科(英文)
[46] 譯注:尼希米為調節氣氛作出的幽默表達。
[47] 譯注:這裡應該是“吃了預備逾越節的筵席”,而不是逾越節的筵席,因耶穌是在逾越節當天上了十字架,祂和門徒最後的晚餐,就是在吃預備逾越節的筵席。
[48] 譯注:俄利根(185年-254年),生於亞歷山大港,卒於該撒利亞,是基督教中希臘教父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亞曆山太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為神學家和哲學家。
[49] 譯注:羅馬帝國皇帝德西烏斯(249-251年在位政)時,在政策上引入一種急劇的變化,使得對基督徒的迫害成為一種遍及帝國全境的系統行為。
[50] 譯注:荷馬,相傳為古希臘的吟游詩人,生於小亞細亞,失明,創作了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者統稱《荷馬史詩》。目前沒有確切證據證明荷馬的存在,所以也有人認為他是傳說中被構造出來的人物。而關於《荷馬史詩》,大多數學者認為是當時經過幾個世紀口頭流傳的詩作的結晶。(維琪百科)
[51] 譯注:文本批評 (Textual criticism),文本鑒別,又稱文本批判、低等批評,是文本考證的一種,是對文稿文本錯誤的確定和勘誤,古代文獻採用手抄形式導致在傳抄過程中會出現錯誤,即使是猶太教中對抄寫正確性有非常嚴格要求的《妥拉》也是如此。在已有傳抄本的情況下,文本考證試圖盡可能重建原始文本的原貌。文本考證的最終目的是產生出盡可能接近原文的“考證版本”。(維琪百科)
[52] 譯注:《六文本合參》(Hexopola),《聖經·舊約》合參本。將《聖經·舊約》的希伯來文本與希臘文本,以及四種希臘文譯本,分六欄並列,以示其異同,並附以各種注解。原作共五十卷,寫於240—245年間。7世紀時佚,現僅存抄本殘篇。為研究《聖經·舊約》的重要資料。
[53] 譯注:《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是新約時代通行的《希伯來聖經》的通用希臘語譯本,估計於西元前3世紀到前2世紀期間,分多個階段於北非的亞歷山大港完成,最遲不晚於前132年。《七十士譯本》普遍為猶太教和基督教信徒所認同。全卷書除了包括今日普遍通行的《聖經·舊約》以外,還包括次經和猶太人生活的文獻。 維琪百科
[54] 譯注:《論首要原理》是基督教思想家首次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論化的系統闡述。基督教經過幾個世紀的急劇發展,已經形成氣候,但教會內部卻形成了各種派別;加上大批知識份子進入教會,產生了對教會原初信仰教義化、體系化的需要,亦產生了多樣化的詮釋和爭執。作為一名有希臘文化背景的基督教思想家,俄利根面對社會知識階層,將原始信仰體系化。但是,這與普通信眾的一般需求有很大的差距,因而無法得到教會的承認。
[55] 譯注:書名原為“The Chronology of the Public Ministry of Jesus”,《耶穌公開服事編年體》,本書認為耶穌服事的時間是三年半時間。作者為喬治·奧格(George Ogg),英文初版於1940年,暫未發現中譯本。
[56] 譯注:泰考尼斯(Ticonius),活躍於370-390年,是4世紀北非拉丁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
[57] 譯注:優西比烏(Eusebius),生於約260年或275年,可能卒於339年,是基督教史學的奠基人。由於他對早期基督教歷史、教義、護教等貢獻,被一部分人認為是基督教史之父。
[58] 譯注:克利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1577-1648,統治59年,是在位最久的丹麥國王。
[59] 譯注:Spanish piece of 8,西班牙銀元或八裡亞爾。
[60] 譯注:湯瑪斯·傑弗遜(英語:Thomas Jefferson,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第三任美國總統(1801年-1809年)。同時也是《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及美國開國元勳之一,與喬治·華盛頓、本傑明·佛蘭克林並稱為美利堅開國三傑。其任期中之重大事件包括路易西安那購地案(1803年)、1807年禁運法案、以及路易士與克拉克探勘(1804–1806)。
[61] 譯注:新約手稿中的“文本變體”(Textual Variant)出現在抄寫者有意或無意地對正在複製的文本進行修改時。對新約的文本鑒別或考證(Textual Criticism),包括對其文本變體的研究。
[62] 譯注:《塔納赫》(Tanakh),是猶太教正統版本的《希伯來聖經》,是猶太教的第一部重要經籍,後來的基督教稱之為“希伯來聖經”或“舊約聖經”。
[63] 譯注:詮釋範疇(Explanatory Scope),指一種理論可解釋的內容之多少。如果一種理論能解釋更多的東西,那麼它的詮釋範疇就更大。
[64] 譯注:他提安(Tatian),亞述人,二世紀基督教作家和神學家。
[65] 譯注:薩迪斯(Sardis)的梅利托(Melito),( – 180),早期基督教的權威。梅利托(Melito)因其個人影響力和文學作品而在亞洲的主教中佔有首要地位,而這些作品大部分都已丟失。然而,已經發現的東西為第二世紀的基督教提供了深刻的見解。
[66] 譯注:《四福音和參》(Diatessaron),是將四福音書編纂為單一連貫敘事體裁的合成書,是敘利亞中東地區的標準福音書文本,在西元400年被四本福音書分別取代。
[67] 譯注:“紙莎草紙66”手稿,簡稱P66,英文是Papyrus 66,是已知存留下來的最古老新約抄本之一,是《約翰福音》近乎完整的手抄本。
[68] 譯注:“紙莎草紙75”手稿,簡稱P75,英文是Papyrus 75,是早期的希臘文新約紙莎草紙抄本。它被認為是迄今發現的“最重要”的新約紙莎草紙抄本。
[69] 譯注:尼西亞大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西元4世紀時,東方教會阿裡烏派關於基督受造而不與上帝同體之說,引起基督教會的辯論和分歧。當時尚未受洗的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為防止異端思想對他所利用的基督教會產生分裂的影響,在尼西亞召開基督教第一次大公會議。經過與會各派的激烈爭論,最後採納教會史家優西比烏提出的信經底本,加入反對阿裡烏派而強調基督一位格和神人兩性的教義,結尾又附加詛咒異端的若干條目,最後經君士坦丁親自審定通過。
[70] 譯注:潘菲勒斯(Pamphilus of Caesarea),是凱撒利亞的長老,是他那個時代的首席聖經學者。
[71] 譯注:《為俄利根辯護》(Apology for Origen),由潘菲勒斯寫的五本著作和優西比烏寫的一本著作合集而成。
[72] 譯注:西元309年,潘菲勒斯與他的家眷,以及其他數位著名教師、跟隨者們,一同被處以死刑。
[73] 譯本:本書為俄利根所著,詳細譯注見上集。
[74] 譯注:《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教會史,在史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該書試圖重現從使徒時代到西元324年這三個世紀的教會歷史。全書共十卷。
[75] 譯注:這段論述選自優西比烏《教會史》第三卷,第二十四章,7。
[76] 譯注:這段話出自優西比烏《福音書的證據》(The Proof of the Gospel)。
[77] 譯注:伊本·埃茲拉(Abraham ben Meir ibn Ezra),是十二世紀猶太裔西班牙學者、科學家、注釋家和詩人。
[78] 譯注:修訂(Emendation),是指在版本文獻學(文本批評)中,編輯對文本中錯誤的更正和改進。
[79] 譯注:新約手稿中的“文本變體”(Textual Variant)出現在抄寫者有意或無意地對正在複製的文本進行修改時。對新約的文本鑒別或考證(Textual Criticism),包括對其文本變體的研究。
[80] 譯注:批判版(Critical Edition),指使用一切現有證據,來嘗試構建一項文本的編輯。
[81] 譯注:新約聖經格雷斯(Novum Testamentum Graece)是《新約聖經》的重要版本,原文為古希臘語,是大多數現代聖經翻譯和聖經批評的基礎。它也因其最有影響力的編輯Eberhard Nestle和Kurt Aland而被稱為Nestle-Aland(尼斯勒和奧倫德)版本。(維琪百科)
[82] 譯注:1908年,德國學者葛列格里(Caspar Rene Gregory)發表《新約希臘文手稿》,嘗試將手稿的查詢編號標準化。1963年,庫爾特·奧倫德(Kurt Aland)拓展了葛列格里的工作,使葛列格里·奧倫德編號(Gregory-Aland)或GA編號成為查閱新約希臘文手稿的工業標準(其它語種使用不同體系)。
[83] 譯注:校注(Critical Apparatus),是在對原始資料進行考證時的一種系統性的標記符號,它以簡明的形式在單個文本中表現該文本的複雜歷史,給勤奮的讀者和學者提供幫助。
[84]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也簡稱PC。
[85] 譯注:蘭貝斯宮(Lambeth Palace),是坎特伯裡大主教在倫敦的官方住所。它位於倫敦蘭柏區,1200年左右被坎特伯裡大主教獲得。
[86] 譯注:第八修正印刷本,2004年。
[87] 譯注:明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unster),位於德國明斯特市的一所公立大學。
[88] 譯注:馮·索登(Von Soden),1852-1914,德國聖經學者、牧師、神學教授和文本理論家。
[89] 譯注:校注(Critical Apparatus),是在對原始資料進行考證時的一種系統性的標記符號,它以簡明的形式在單個文本中表現該文本的複雜歷史,給勤奮的讀者和學者提供幫助。
[90] 譯注:休戰紀念日(Armistice day),每年11月11日紀念一戰盟國與德國于淩晨5:45在法國康比涅簽署的停戰協定,該停戰協定生效於1918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十一點”。人們一般會佩帶罌粟花,以紀念陣亡將士。
[91] 譯注:T&T,這裡指2005年出版的德語著作《Text and Textwerk》的簡稱。
[92] 譯注:《六文本合參》(Hexapla),也有譯作《六經合璧》,指西元240年由神學家和學者俄利根編纂的六種不同文本合集的舊約聖經。
[93] 譯注:人物簡介參照前面。
[94] 譯注:人物簡介參照前面。
[95] 譯注:人物簡介參照前面。
[96] 譯注:《伯撒抄本》(Codex Bezae),是一部新約聖經手抄本,可追溯至西元5世紀;其中包含了大部分希臘文和拉丁文版本的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以及《約翰三書》中一小部分。《伯撒抄本》是西方文本類型(Western text-type)的代表性抄本。
[97] 譯注:《詩歌智慧書》(Ketuvim),是指基督教《舊約聖經》中除《律法書》、《歷史書》、《先知書》之外的幾卷書。
[98] 譯注:“紙莎草紙115”是用希臘語寫在紙莎草紙上的新約聖經的零碎手稿。它由26個抄本片段組成,其中包含《啟示錄》的各個部分,可能僅此而已。它可以追溯到西元三世紀。(參考維琪百科)
[99] 譯注:新約手稿中的“文本變體”(Textual Variant)出現在抄寫者有意或無意地對正在複製的文本進行修改時。對新約的文本鑒別或考證(Textual Criticism),包括對其文本變體的研究。
[100] 譯注:“Patterns of Evidence: The Moses Controversy”暫譯《證據模式:摩西的爭議》,是一部英文紀錄影片和同名書籍,揭示了摩西書寫聖經前幾卷書的最新驚人證據,並說明為何當今主流學者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
[101] 譯注:聖經博物館是華盛頓特區的一座博物館,記錄了聖經的敘述,歷史和影響。它於2017年11月17日開業,有1,150件永久收藏品和2,000件其他機構和收藏品的借閱品。
[102] 譯注:畢士大,英文Bethesda。
[103] 譯注:聖亞納教堂(The Church of St. Anne)是耶路撒冷舊城內的一座教堂,位於穆斯林區,靠近畢士大池考古遺址。目前的教堂為羅曼式,由十字軍興建於1140年。(維琪百科)
[104] 譯注:基訓泉是古代大衛城的主要水源。 基訓泉雖然位於城牆外, 但由於距離不遠, 泉水可以順利引入城內的輸水道和11米深的井穴。 耶路撒冷的居民不必到城外取水。
[105] 譯注:喬治·路易士·科斯坦紮(George Louis Costanza)是傑森·亞歷山大(Jason Alexander)在美國電視情境喜劇《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中的虛構人物。
[106] 譯注:NRSV,新修訂標準版聖經,New Revised Standard Bible。它是1989年出版的《聖經》的英文譯本,完整的譯文包括標準的新教正典書籍以及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基督教傳統上所包含的次經書籍。
[107] 譯注:盎博羅削圖書館(Biblioteca Ambrosiana)是義大利米蘭一座歷史悠久的圖書館。它得名於米蘭的主保聖人盎博羅削,由樞機主教費德里科·博羅梅奧創建,其代理人遍及西歐,甚至遠達希臘和敘利亞,尋找書籍和手稿。 (維琪百科)
[108] 譯注:點球成金(Moneyball),是一種數學理論和一部美國電影的名字,表示“以弱勝強”、“逆境中制勝”等概念。
[109] 譯注:領域在這裡可能是指“融合邊界(Eruv)”,尼希米沒有細說。
[110] 譯注:《米書拿》在這裡講,木筒是一種測量工具。
[111] 譯注:指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著有《猶太古史記》。
[112] 譯注:書面妥拉,又稱妥拉或摩西五經。
[113] 譯注:祈雨舞早在古埃及時就有,從時間上來說,是早於摩西時代。
[114] Yeshua,耶穌的名字,意思為“耶和華拯救”(Yehovah Yoshia)。
[115] 譯注: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是古希臘神話中的醫神,在古羅馬神話中被稱為埃斯庫拉庇烏斯(拉丁語:Aesculapius),他是太陽神阿波羅之子,形象為手持蛇杖。
[116] 譯注:差遣,the Sent One,也是送來,對比於“送來的池子”。